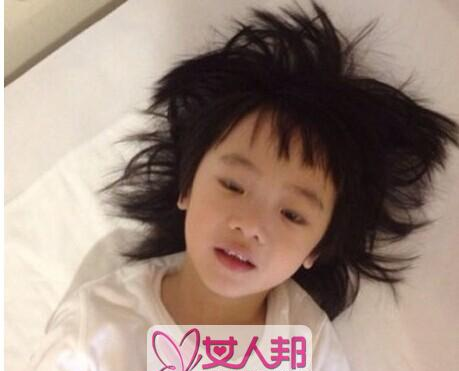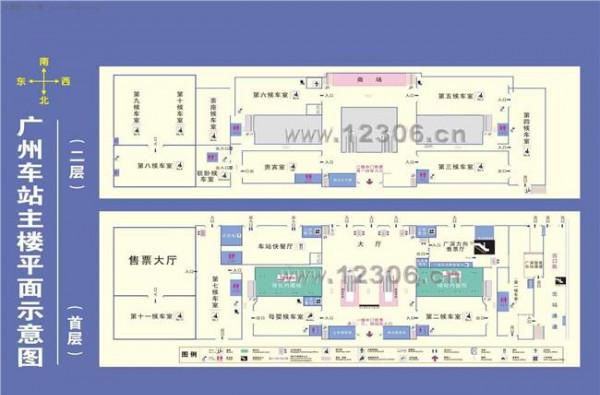欧洲警察 难民逃亡路上女性常遭性侵 施暴者包括蛇头和欧洲警察
“大家都知道,给蛇头交走私费有两种方式:交钱或者出卖自己。”萨马尔说。
偷渡欧洲的难民不仅面临各种艰难险阻和生命危险,不少女性难民还受到性侵的威胁。据《纽约时报》1月2日报道,在德国,一名叙利亚女子为了偿还丈夫欠蛇头的债,被迫在走私路线上充当性工具;另一名妇女在拒绝匈牙利警卫的性要求后被打昏。还有一名女性难民曾经是一名化妆师。她为了避开同行男性难民的注意,刻意将自己打扮成男子的模样,并不再洗涤衣物。在位于柏林的避难所,她晚上依然和衣而睡,并用壁橱堵住门口。“这里没有锁,没有钥匙,什么都没有。”这位名叫Esra Al Horani的化妆师说。《纽约时报》指出,她是少数不怕被点名的女性之一。霍拉妮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她说她“只遭遇过殴打和抢劫”。据《纽约时报》报道,从中东逃往欧洲的难民面临着许多困难——国内战争和暴力、蛇头的残酷压榨、危险的海域、陌生大陆上未知的未来。女性难民面临更多风险。根据对几十名移民、照料难民的社工和心理学家的采访表明,针对女性的暴力在这一波难民潮中时有发生。此类暴力行为包括强制婚姻、强迫卖淫和家庭暴力,施暴者包括同行的难民、蛇头、男性家族成员,甚至欧洲警察。今年10月,BuzzFeed还关注了难民逃离途中妇女儿童面临的潜在威胁。根据这份报告,妇女和儿童很容易受到有权有势的男人的侵犯和胁迫。当难民穿越欧洲中西部时,女性难民也面临着性侵犯的问题。在德国柏林的一个难民营里,霍利尼仍然穿着衣服睡觉。
逃到欧洲的难民男女比例3:1为了逃离战争和贫困,2015年有100多万难民从中东移民到欧洲。根据联合国统计,在前往欧洲的难民中,男女比例为3:1。“男人占了上风,包括数量和地位。”德国人权研究所性别研究专家海科·拉贝说。苏珊娜·霍内是柏林西部一家心理治疗中心的首席治疗师,她专门负责治疗女性难民的心理创伤。霍内和她的18位同事每2周为每位女性难民提供一次心理咨询,并提供7个小时的社工服务,包括家访以及帮助她们适应在德国的生活。苏珊娜·霍恩说,她负责治疗的44名女性难民几乎都经历过性暴力。“在我们听完这些女难民讲述自己的经历后,我们不得不定期去看心理医生。”一名现年30岁的叙利亚女子在2015年初时,与家人共同逃难。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到达保加利亚时,她的丈夫无力向蛇头支付偷渡费,于是将妻子交给了蛇头。在接下去的三个月内,为了让家人能够继续偷渡行程,她几乎每天被强奸一次。不久后,她的丈夫也开始虐待她了。“这个逻辑真的很奇怪。”霍恩说,“他显然是妓女,但他觉得受到了侮辱。相反,他的妻子成了错误的一方。”这名女子目前获得了庇护,与孩子共同在柏林生活。她的丈夫目前在德国的其他地方。由于在柏林街头跟踪她,她的丈夫被判处禁止令。但是,这名女子仍然不敢透露自己的名字,担心遭到丈夫或其他家族成员杀害,因为她令家族“蒙羞”。霍恩说,这名妇女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所有症状,包括闪回、失眠和注意力不集中。“这一刻她可能好好的,下一刻她就会在椅子上背对着你,回想着在大马士革躲避子弹的日子,或在保加利亚遭受虐待的场景。”霍内说道。“这里的女人生活在男人的阴影下”据《纽约时报》报道,希腊是难民进入欧洲的主要入口之一。在这里,接待中心常常人满为患,照明不足,而单身女性缺乏个人空间。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威廉·斯宾德勒说:“男人、女人和孩子睡在同一个区域。在整个欧洲,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收到了许多关于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的报告。”《纽约时报》指出,甚至是在相对安全的德国,面临着100万名难民的重压以及物资运输难以为继,整个庇护体系摇摇欲坠,已经难以为妇女提供基本保护——比如带锁的卧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避免人们无家可归。”德国性暴力专家拉贝说,“但一个有利于性暴力的环境是一个风险因素。我们不应该让安全标准下降。”但是,在柏林东部管理两处庇护所的舍鲍姆表示,“说”总是要比“做”更容易。他所管理的两处庇护所每层有两个浴室,所有房间均已满员。化妆师霍拉妮就在这两处庇护所的其中之一。那里有120名成年难民,大多数是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其中80人为男性。“这里的女性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下。”舍鲍姆说,“她们的声音被淹没,这是个问题。”德国法律很难处理难民家庭暴力柏林庇护所在当地咖啡馆组织的女性“咖啡时间”的夏日舞蹈。
在志愿者分发热汤和新鲜水果的食品站,女性往往排在队伍的最后。她们长时间地呆在房里,很少参加公告板上公示的活动:例如参观博物馆或听音乐会。一名叙利亚妇女抵达德国两个月来从未离开过大楼,因为她还未到达德国的丈夫禁止她出门。在干洗房,女人之间小声聊着家暴的传闻:比如四楼的吃醋丈夫打了妻子、一名妇女因为不能生育而遭到丈夫殴打。几个月前,两名阿富汗男子骚扰了一名阿富汗女孩,并将她推下自行车。幸运的是,她周围的人及时阻止了她。然而,关于暴力事件的报道并不多。据庇护所方面称,已婚夫妇从来不分开,从而使女性更为依赖丈夫,而不愿与丈夫分离。理论上,德国法律足够健全,能够处理家暴问题。但在实践中,很难在庇护所实施夫妻分离这样的措施。我第一次接到家庭暴力的报案,舍鲍姆就报警了。令他惊讶的是,遭受家庭暴力的妻子声称,舍鲍姆“想带走她的丈夫”。此后,他大多采取调解家庭暴力的方式,尽最大努力争取女性在家里的地位。上个月,舍鲍姆手下的一名志愿者组织妇女开展了一次户外散步。这一次,即使是猜疑心最重的男子都允许他们的妻子参加。这次活动中,一名妇女首次离开庇护所。在公园中,她用手机放了一首歌,并跟着歌声翩翩起舞。“我们在户外待的时间越长,她就越有信心。”一位名叫薇薇安·鲁斯的志愿者回忆道。她是一名34岁的瑜伽教练。现在还有只有女性参加的编织课程和有氧健身课。每周三早上,女性成批来到一名志愿者的家中进行私密沐浴,并参加美甲和化妆课程。女性社工每周留出一个下午,组织女性难民去街对面的咖啡馆参加“咖啡时间”活动。咖啡馆的装修虽然是欧式风格,但只要Hollani一用手机播放阿拉伯音乐,整个咖啡馆就会立刻变成舞蹈和头巾的海洋。一些妇女开始在手上纹身,而另一些妇女则开始抱怨成为难民的痛苦。“交钱或卖身”35岁的萨马曾是叙利亚财政部的一名员工,她对女性在移民过程中遭受的苦难有着深刻的记忆。萨马尔在大马士革郊区的家在内战中遭到轰炸,她不得不带着三个女儿在漫长的逃亡路上走了14个月。“我不允许她们离开我的视线,一分钟也不行。”她用阿拉伯语说,并通过翻译转述。在沿途中,她和其她单身母亲轮流睡觉,互相依靠并照管对方的女儿。然而,在土耳其,萨马尔在准备登上一艘前往希腊的船时遭到抢劫。她付不起走私者的钱。一个叫奥马尔的人走过来,提出只要和他睡觉,就免费带走他们。在客栈里,与其他女难民交谈时,撒马尔听说过这个人,会让她们“去那个房间做那件事”。“大家都知道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向蛇头交偷渡费。”她说,“交钱或卖身。”但她拒绝了,这激怒了奥马尔。那天晚上,他闯入撒马尔的房间,威胁她和她的女儿。萨马尔尖叫着把他吓跑了。萨马尔在土耳其工作了近一年,才攒下了4000欧元用于接下来的旅行。在城市的另一头,霍内对女性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她表达了另一种观点。“这个问题很难处理。我们不可能让庇护所只接受女性,因为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全家在一起。有些女性需要男性的保护。”霍内表示,“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很多男性也遭受心理创伤。谈不上是非黑白与善恶。如果要帮助妇女,我们也要帮助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