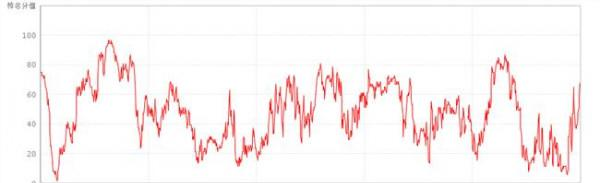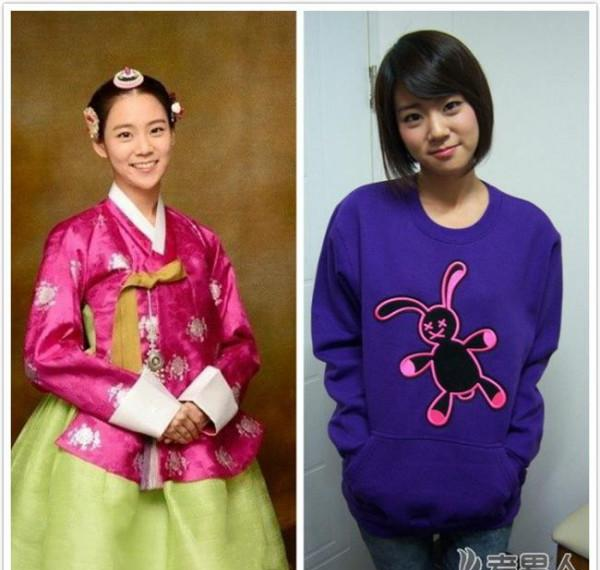土亚 亚美尼亚大屠杀100年:土耳其为何拒绝承认“种族灭绝”
今天的世界对二战中的纳粹暴行早已达成共识,那是一场可怕的种族灭绝,但包括亚美尼亚大屠杀在内的诸多历史惨剧,至今多方仍然各执一词。事实上“种族灭绝”是个二十世纪发明出来的新词,最早在1943年被一位波兰犹太人律师拉斐尔·莱姆金用来控诉党卫军针对肉体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然而莱姆金却从未将一百年前制造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土耳其青年党等同于纳粹。1915年到1918年之间,超过50万亚美尼亚人遭到杀害,甚至还有人估计,到1922年遇难人数已至150万人。
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馆
对这起一战期间所发生的惨案的定性,很大程度上出于战后世界对种族主义的政治清算:1939年希特勒就入侵波兰发表演说时说:“……无情地让死亡降临波兰,无论男人、妇女还是儿童,只有这样德意志才能获得生存空间……毕竟现在还有谁会说起亚美尼亚呢?”纳粹德军在占领区展开“德意志化”,试图同时在文化和人口结构上把波兰抹去。这同二十多年前的土耳其青年党如出一辙,将异族驱赶出家园,建立民族纯净的新国家。今天土耳其政府试图将其叙述成战争期间难以控制的悲剧,正是因为其对纳粹党的启示意义,而难以撇清与法西斯主义的间接联系。地缘政治的十字路口 展开近东地区的地图,你很快就能明白亚美尼亚这个高加索小国的苦难源头何在,她被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夹在中间,几乎正好嵌在历史上三个文明世界之间的交叉路口:西邻奥斯曼腹地,向东可以进入波斯世界,而北面则是巨大的俄国。再往前看,马其顿、东罗马、萨珊王朝和阿拉伯帝国都曾逐鹿于此,而亚美尼亚这个古老的民族却从未被真正征服过,为了防止被毗邻强权同化,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使其语言文字和民族主体性能够在之后一千多年里幸存于外族统治。 为了生存,亚美尼亚人在与帝国和王朝打交道时精明而谨慎,这使得他们很容易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大屠杀的悲剧源于一个地区大国的沉没和崩溃。 亚美尼亚人曾经密集地定居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作为生活在奥斯曼“哈里发国”的少数民族,他们被赋予了宗教和文化上的高度自主,这一社区也是历代苏丹所赏识的顺民。然而在政治动荡的帝国晚期,亚美尼亚人,连同帝国内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一起,加入到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并且同俄罗斯和希腊人一样皆信奉东正教,亚美尼亚人与这些东欧“表亲”之间的好感与生俱来,这令当时与德国结为盟友加入一战的奥斯曼帝国惶恐不安。在帝国内部,日后建立当代土耳其共和国的“青年党人”视亚美尼亚人为眼中钉,这些倡导激进改革的少壮派军人要求建立一个彻底“土耳其化”的新土耳其,奥斯曼允许多民族共存的“米利特”制被视为落后的根源,更不允许一个与劲敌俄国关系暧昧的族群存在于土耳其境内。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高加索地区,各族群高度混居的民族“马赛克” 这也是土耳其今天拒绝承认“种族灭绝”存在的原因。土耳其政府坚称亚美尼亚悲剧是“混乱时期造成的一系列混乱悲剧”,也是一战的受害者..的确,“青年党”有充分的理由敌视当时的亚美尼亚人,整个近东世界是一个民族的马赛克,煽动居住在邻国的东正教徒煽动叛乱是俄罗斯人的惯用伎俩。事实也证明,亚美尼亚的参与导致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地区惨败。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驱逐潜在敌人在当时是合乎逻辑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并没有炮制出“最终解决方案”——将从肉体上消灭一个国家作为一个项目。但对于“青年党”来说,亚美尼亚的民族问题是新土耳其能否在战争中诞生。要么让民族“马赛克”继续维持,接受少数民族引狼入室,以外国势力接近威胁完整的土耳其国;或者干脆打破“马赛克”,用单一民族重组国家机器,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杂居问题。土耳其选择了后者。建立现代国家的代价 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迹?历史至少给出了三条重新划分民族国家的道路: 1)以族群和语言为单位重新划分国界,这是英法在解决殖民地纷争和民族独立的惯用做法,我们今天看到的印巴分治,以及一战后确立的中东欧格局,皆以此为依据。如果土耳其以此立国,其领土将会收缩至君士坦丁堡以西的色雷斯以及小亚细亚沿岸,而亚美尼亚人将占据着东安纳托利亚至高加索的大片区域,另外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一带,则可以成为另一个希腊人国家; 2)以山川为界的人口和领土交换,是棍棒下的强制迁徙。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斯大林解决了波兰和乌克兰之间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在共产主义阵营一盘棋的指导下,说波兰语的被送到河西,说乌克兰语的被送到河东,说德语的可以被送到西伯利亚苦役。后来,土耳其共和国还与希腊达成了人口交换协议。卡帕多西亚过去几乎是一个说希腊语的地区。当地居民仍在使用早期基督徒留下的岩石教堂。今天,没有希腊的痕迹;同样,今天在希腊也很难找到奥斯曼占领留下的清真寺和穆斯林纪念碑。 3)集中屠杀,把特定族群集体视为政治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大林和希特勒,当然斯大林的民族驱逐并不是像纳粹那样以消灭种族为终极目的。但驱逐总是伴随着屠杀,臭名昭着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为了解决被驱逐犹太人的集中管理问题,“自然而然”达成的最终步骤。而土耳其在一战期间的所为与纳粹的距离,也许仅仅是少了高效运作的文官系统,和个别几个异常冷酷的头脑。第三帝国的合法性几乎全部来自排斥一切“非德意志”的元素。 在以上三种选择中,我们今天可以推测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所作所为,可能在指导思想上接近第二种,但实际上则不由自主地导致了第三种的后果。就如同二战末期及战后德国东普鲁士领土上被驱逐的德意志族一样,驱逐者总是一支构成复杂的暴徒队伍,当时的苏联红军中不乏被释放的囚犯和未经训练的中亚民族;土耳其军队中则混杂着各种民族沙文主义者和仇恨基督徒的圣战者。在国家失灵的情况下,这些军人就变成了有组织的屠夫。在以上三种选择中,我们今天可以推测,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所作所为在指导思想上可能接近第二种,但实际上却不由自主地导致了第三种。就像二战结束和战后被驱逐出德国东普鲁士领土的德国人一样,驱逐者始终是一个复杂的暴民团队。当时苏联红军中有许多被释放的俘虏和未经训练的中亚民族;土耳其军队混杂着各种国籍的沙文主义者和仇视基督徒的圣战分子。当国家失败时,这些士兵就成了有组织的屠夫。
近代洋务改革时期的伊斯坦布尔老城
纪念或遗忘,都是政治 当欧盟敦促土耳其承认并反思这场“种族灭绝”时,它或多或少带着审视纳粹的眼镜看待历史。如果土耳其接受“种族灭绝”的定义,就等于承认现代土耳其的开国领袖等同于罪犯和暴徒,甚至动摇了现代土耳其的合法性。这个崭新的国家仍然面临的现代化进程,如世俗化、民主化和与传统的对话,将受到阻碍。今天,土耳其仍然需要尝试回答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东方还是西方?西化还是伊斯兰?独立还是做地区领导?这个国家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国家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土耳其人仍然在这些关于他们的身份和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今天的土耳其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侮辱土耳其”,连同亚美尼亚大屠杀在内的许多同周边国家有关的敏感议题,都有可能因为冒犯Turkishness而被问罪。那些今天被称为“国父”的青年党人,当年用枪杆子切断自己同“非土耳其人”之间的联系,并让西方屈服于新生的政权,今天真的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则需要面对昔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亚美尼亚大屠杀则正好是土耳其建国道路上一块沾满了鲜血的垫脚石,若土耳其没能正确处理好这笔旧账,就会被理解为不择手段地牺牲昔日奥斯曼帝国少数民族的利益,来换取一个所谓“进步”的现代土耳其。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今天土耳其的官方立场已经开始向对大屠杀“负有责任”渐渐转向,不得不说这也是担心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妥协。其总统和总理纷纷通过不同渠道向亚美尼亚发出声音,表示对这桩历史惨案中的受害者表达同情。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提到大屠杀与土亚关系时,也避免使用“种族灭绝”提法,作为北约盟友,土耳其在近东地区的价值让美国官方对历史的评价也不得不服从于现实政治。 从亚美尼亚的角度来看,建立一个民族国家需要与自己的过去进行协商。独立的亚美尼亚才脱离苏联20多年。最后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家是在公元9世纪。作为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大屠杀成为其自身脱离苏联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亚美尼亚全国纪念大屠杀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独立日。这是一个选择集体苦难作为历史起点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土耳其和亚洲未来如何解读这段历史,都只关乎建立自己当代身份的政治。只是当我们在争论土耳其人到底做的是“屠杀”还是“灭绝”的时候,现在还有谁会谈论一战中的近东和中东?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都被迫卷入一场原本不属于他们的战争,让原本和平共处的族群投靠大国,这是东方各民族共同的悲剧命运。 1914-1918年,整个奥斯曼帝国总共约有430万平民遇难,占帝国总人口26%,他们来自各个“米利特”社区。一战结束后的欧洲秩序:图中可以看到希腊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和爱琴海东岸,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退缩至小亚细亚内陆,而亚美尼亚人当时仍定居于安纳托利亚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