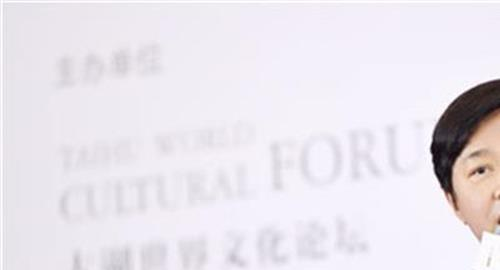卦理僵神 思想史上的今天 为何周予同批学校读经“僵尸出祟”
今日经学之热,超乎想象。有学者认为,经学为国学之本。而我们都知道,国学不仅已经为教育部设为一级学科,而且,也已进入了中央党校,成为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程。六月份还有着名学者表示,要把经学还原成一棵生命不息的大树。基本意思是两个。一个意思,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根本,抛弃经学意味着斩断自己的价值之根,由此,我们必然先是“苏化”,然后“西化”,就是没有“中国化”。另一层意思,涉及经学如何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对经学进行注疏就是发展经学的最佳途径。虽然笔者很纳闷,这两层意思之间是否存在紧张、矛盾?因为一旦考虑到对经学进行现代的注疏,那么,这样阐述出来的东西是否还是经学,显然是值得发问的。如果考虑到经学在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声名狼藉,这样创造出来的新东西是否换一个名字会更好?但也许这些想法都是二心。第一个位置的问题是,什么是儒家经典?当我们谈论儒家经典的价值时,不要忘记,价值是基于事实的。先搞清楚儒家经典的本义,再谈其他。1926年10月5日,周予同先生发表于《一般》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的文章或许可以从一个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经学。只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放在今日肯定要被口诛笔伐。它叫《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
周雨彤
顾名思义,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是当时学校主张读经。具体而言,周予同先生看到1926年8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刊载的一则新闻:江苏教育厅于八月八日训令省立各校,开展读经,“读经一项,包括修齐治平诸大端,有陶冶善良风俗之作用,似应由各校于公民科或国文科内,择要选授,藉资诵习。”而之所以主张在中学读经,理由和今日略有差别。“惟中等各校,学生年龄大率正在青春时间,定识定力,均尚未有充分修养,似应一律禁止男女同学,以防弊害,而肃风纪。”也就是说,中学男女学生正处在青春萌动时期,但是认识的充分性和意志的坚定性都不够,因此需要经学加以教育,加强修养,以防事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该训令并不要求小学或大学读经。理由是,小学生对于男女之防并无认识,而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当自我负责。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江苏教育厅的经学教育还是有覆盖面不足的问题的。今日小学生的读经班屡见不鲜,大学呢?国学一级学科就是针对大学的。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之所以读经的理由已然不同。今日读经,重点不在对男女大防有所认识,而是有着更深的关怀:按照开头那些专家的说法,是为了寻找民族价值之根。在那篇文章中,周予同先生从两个角度批评了读经运动。一个角度涉及儒家经典的定义。他的基本意思是,对于什么是儒家经典,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认为读经是假的。周予同先生认为,关于经学的定义,至少分为四种:骈文学派,经古文学派,经今文学派,以及古史辨派。骈文派起源于清代阮元的古文理论,在近代刘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命题。他们认为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因为六经中的文章多为奇、偶,声韵和谐,海藻画一章,是骈文体,就像丝绸的经纬一样,所以被称为经典。从这个标准出发,其他非儒家的书,只要也是骈文,也可以称为经。比如老子叫《道德经》,《离骚》叫《离骚经》等等。周予同先生承认,这种说法过于宽泛,混淆了文学、哲学和公认的儒家经典。问题是,这毕竟也是一种说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主张读经的圣贤是否也主张读文学?必须指出的是,周予同自己也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同时,主张读经的人心目中,经学如果不是今文经学意义上的,就是古文经学意义上的,读骈文说也是不认同的。那么,从比较经典的古文经学的角度看,经学又是什么?周予同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经典中的经典只是书籍的总称,而不是孔子六经的专有名词。在孔子之前,有所谓的经书;孔子之后,还会有一批可以称为经书的经书。这里的重点是,经是点书的线,“所以只要是连线的,就可以叫经”。中国古代最后一位经学大师章太炎在《论民族遗产的平衡》中也明确说过类似的话:“是有原因的,绳子和线是和经学联系在一起的。”在《原经》中,他引用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军事书籍、法律、宗教命令、历史、地方志等学者都是经典。显然,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经显然不能以是否出自孔子为断。这种说法对经的范围持开放的态度,其实高度肯定了中国人的未来的创造性;否则,一方面固然“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在孔子巨大的权威的压制之下,沦为附庸。从这个角度看,开头提到的某位专家所说的今日经学的重要任务是进行现代的注疏,这种说法难免还有抹杀中国人的主体性,把自己看作孔子附庸的痕迹。试问,为什么我们后来的中国人不能创造新的经典,而必须处在注疏的地位上呢?但换个角度看,似乎削弱了景的崇高地位。因为很显然,从这个定义出发,任何一本书,只要用线装订,都可以成为经。另一方面,也必然存在一些悖论:在线装衣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少数文人特殊爱好的情况下,胶装的古代经典能称得上经典吗?如果说这是因为时代不同,装帧形式发生了变化,对具体内容没有影响,那我们后来的中国人还能创造经典吗?电子技术创造的东西能算作经典吗?从这个角度来看,用订书的路线来定义佛经是简单粗暴的,抹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周予同先生认为,主张读经的人们恐怕对于经古文经学意义上的经也并不认同,这种意义的经还是过于宽泛。于是他们乞灵于今文经学派。这派认为只有孔子的着作才能称为经。所以,经的领域只有如下内容:《诗经》三0五篇,《书》二十八篇,《仪礼》十六篇,《易》的《卦辞》《爻辞》《象辞》《彖辞》四种,以及《春秋》经本文。连一般似乎毫无疑问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不能算。要命的是,《诗经》中还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句,这显然和当时江苏教育厅主张读经的初衷相违背的;何况,老实说,“断烂朝报”似的《春秋》非常不好读。以上三种对经典的解读,至少可以和孔子有关系。古代史派明确切断了孔子与经典的联系。在他们看来,五经是五种不相关的杂书,孔子与它们无关。如钱通过繁复而扎实的考证,指出《诗》是最早的集子;书是三代中的“文献汇编”或“档案集”;《仪礼》是战国时期随意抄写的伪书;《易经》中的原始占卜是生殖崇拜时代的象征,后来被孔子之后的儒生用来发挥自己的仁义;《春秋》是流水账,是“破朝报”。当然,今日看来,古史辨派的观点可以被归为二十世纪文化激进主义的脉络之中,因此似乎是应被忽略,甚至应被嘲笑的。宽容的看,古史辨派只是否定了经和孔子之间的联系,而没有完全否定经作为某种文化典籍的事实性存在。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说,虽然经不是孔子独创的,但它们是中国人祖先创造的,里面不乏智慧的结晶。事实上,这个立场可以应用到骈文派、古文经学派身上。经虽然可以是广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义的经就是没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有的专家学者主张从经学中发现中国文化价值之根,也有一点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是不是就是通常所理解的那一些?这才是争论的焦点之所在。不可否认,周予同先生从经典的多元化定义出发,对经典阅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逻辑上有了飞跃。但是,他的真实意思很明确:如果所谓的经典就是那些,不管是五经还是十三经,那就洗洗睡吧。个人认为五经、十三经之类的还是可以读的,但同时又要读其他的书。最起码大家都是线装的。阅读的顺序是什么?周予同先生对读经运动的第二层批评,和他的切身经验有关。他发现,每一次主张读经之后,总会发生历史事变。民国四年徐世昌主张读经,其后便有袁世凯之称帝;1925年章士钊持教育总长的权威主张读经,不久便发生“三一八惨案”。由此他便担心江苏教育厅的主张也会有伴有不良的后果。今日看来,周予同先生的这些论述显然是经不起休谟般的哲学思维的推敲的。不能因为以前主张读经便伴随着不良后果,就认为只要读经就会产生恶果。不过,也许对于我们的质疑周予同先生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第一次的帝制,第二次的惨杀,固然不能说全源于读经,但它的确是反动行为的预兆呢!”预兆,便有点神秘主义的味道了。科学昌盛的今天,似乎不可信。最后要说的是,周予同先生的这篇文章收录于其文集《经学与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可惜笔者以前都没注意到,这次是在8月份的上海书展上发现而买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