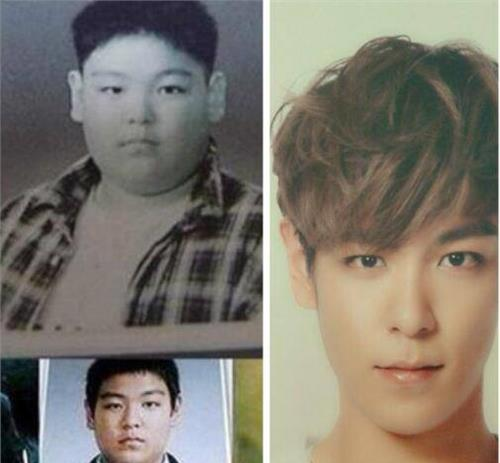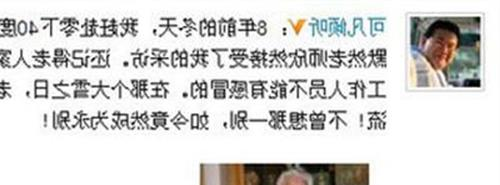cheers怎么读 刘绍铭:余国藩拿起酒杯祝酒时 说的不是“Cheers ”
安东尼.余秋雨。
我最后一次收到余国藩教授的音讯是一封发自去年1月15日的电邮。英文写的,长近两页,偶然一两句也用中文,说自己因心脏手术做了八个多小时,因此自觉经历过一次“死里逃生”。他说自己康复得不错,只是此生“may have to be under medication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e days of Bombay Sapphire martinis and Black Labels and single malts may be over for me, but thankfully, the days of wines, if not roses, still are permitted in measured doses”。大概是1973年夏天,郭帆去远东旅行,路过夏威夷。他写信给我说,他会和我一起吃午饭,用粤语谈论这个世界。既然他已经到了檀香山,我带他去大学附近一家波利尼西亚风味的观光餐厅吃午饭也是顺理成章的。我们点了一瓶夏敦埃酒,服务员说还不错。还记得郭帆拿起酒杯敬酒时,没有说“干杯!”还是“为了你的健康”,而是:“乔,让我们为李家干杯!”我听后有点愕然,只好随口附和着说:“Let's drink life to the lees!”国家口音没有变化,遇到家乡的老朋友,越来越激动。我已经忘了吃那顿午餐花了多长时间。我还记得我们几乎是最后一批不好意思离开出去喝咖啡的客人。关于托尼的人生经历,在这次见面之前我了解的不多。我只知道他出身名门后,父亲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民国陆军上将于伯权将军。国藩的祖父余芸,英国牛津大学出身。1946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余伯泉将军奉命率领国府军事代表团进驻联合国。国藩时年八岁,祖父希望他能留在香港打好中英文根底,一口答应留港看管孙子。祖父当年是香港政府的高级“视学官”,旧学根底深厚,尤善古诗词。郭帆告诉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六年,是他最不寻常的幸福日子。看来余云先生真是一个难得的开明人物。那一年,中央剧院或女王剧院的娱乐节目在周末上午11点为孩子们安排了特别节目。只要老先生能拿到文件空,他就会对可爱的太阳说:“我们去看演出吧。”“正片”通常都是牛仔片,出场前的二十至三十分钟的“序曲”才是小朋友的“戏肉”:卡通片。意想不到的是美国人的cartoons对香港的余家祖孙二代居然是“老少咸宜”。Tony笑得几乎要在地上打滚不在话下,最难得的是爷爷也一样忘形。散场后爷爷还跟孙儿就刚才看过的卡通重温一番。国藩记得爷爷数卡通风流人物时,最爱的三条“汉子”是Bugs Bunny、Tom and Jerry。根据郭帆的说法和散见于《中国遗产季刊》等刊物的零星信息,余云对孙子的“以身作则”无疑是“离经叛道”。他爱哄陪孙子去剧场看动画片。恐怕同行中的资深学者摇头叹息的是,这位“视觉学官”周末去好莱坞老书店逛的时候,还让在天主教华仁学院读书的孙子跟着。郭帆迷上了武侠小说。难得的是,老人不仅没有阻止他在书店“装钉”,有时还会挑选一些孙子孙女最喜欢的礼物。余国藩拿的是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母校任教,是芝加哥大学唯一由神学院、比较文学、英文系、东亚系及社会思想委员会五个院系合聘的教授。国藩逝世后,同事和朋友纷纷为文或留言悼念他。温迪·多尼格是神学院的宗教历史教授。她曾经和曾国藩一起教过“恶的神话”这门课。她说,余教授认为,文学与宗教的讨论应该放在一个理论框架内,并为此树立了榜样。多尼格眼中的托尼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在教学的时候说话很好,很少看他带来的笔记。国藩夫妇生性好客,不时亲自下厨,招呼同事和研究生到家里吃饭。Doniger教授曾是座上客,因有此说:Friends and colleagues recalled Yu's excellent taste in wine and fondness for gourmet cooking. “That was one of the great pleasures of knowing Tony——you ate very well.” Doniger said. They also remember him as a devoted husband and father。多尼格教授看起来没有错,也没有说错。托尼知道生活。他不崇拜物质,却懂得享受,认为物欲的满足是推动进步的动力。有一次,我去芝加哥看他,因为一个会议。他请我去莫顿牛排馆吃饭,饭后带我回家喝两杯成人饮料。我们去了他认识的酒店,买了他说的成人饮料。他在架子上找到了黑带约翰·沃克。走着走着,他还看到了令人敬畏的“皇家礼炮”。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可惜下一个是穷酸买单,但王子的味道就在上面!这话怎么讲呢?“王侯口味、叫化工资”?国藩招待我在Morton吃饭,花了不少钱,我拿着那瓶“皇家敬礼”正要向他敬礼,他一口拒绝,说:“慢着,以我们今天寻常百姓的收入喝这种富贵人家的金汤玉露,不但是一种unseemly extravagance,而且,像广东人说的,有点‘折堕’。我们将就行者上路吧。”芝加哥大学郭帆得意弟子李颖让我为他负责组织的于国范教授纪念画册写点纪念词,说说过去的老游,字数和书名不限。既然“话题是非正式的”,那就好办了。多尼格教授提到托尼喜欢美食烹饪。郭帆和妻子普丽西拉都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广东人。虽然他们的饮食习惯早已西化,但他们在闲暇时还是会和香港游客、朋友聊天。话题一涉及到香港的美食烹饪,他们的口味马上就会“回祖归宗”,说他们午夜梦回吃的就是一碗馄饨面。“这是加拿大文明的精髓”,他说。就我所见,国藩芝大同事写的纪念文字中,神学院院长Margaret M. Mitchell的话最中肯:“Professor Anthony C. Yu was an outstanding scholar, whose work was marked by uncommon erudition, range of reference and interpretive sophistication …… Tony was also a person of inimitable elegance, dignity, passion and the highest standards for everything he did.”国家和诸侯待人接物,广交朋友。他“惊世骇俗”的脾气对朋友和学生都管用,教会人们“皇帝不急,太监急”是真的。难怪埃里克·齐奥尔科夫斯基在成为老师后错过了他的第一位老师,他说:“他表现出了一种热情和强度,这是任何有幸成为他学生的人都无法比拟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念文学的“华人子弟”,平日见面聊天好以金庸小说人物作话题。《射雕英雄传》里大有来头的分别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夏志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口气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一鸣惊人。他“武功”了得,落户的“码头”又是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同学间因应他这些条件,私下称他为“东邪”黄药师。先生那时常替台湾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写文章。同学要是看到家里寄来的报纸有他的大作,总忍不住电话相告:“黄药师又出招了!”只有读过金庸小说的粉丝才知道这些时间灰烬的把戏。夏志清的哥哥季夏安,连珠炮似的背诵金庸的作品,而“恶”的弟弟夏志清教授,则视武侠小说为淫秽和偷盗,一生都不认识金庸。在我和知青先生的通信中,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为什么有“东邪”这个外号。他不知道药剂师的来历,所以不会被逗乐。八十年代中的一个秋天,我到纽约开会,顺道去看夏公。笑谈间我终于有机会亲口告诉他,十几二十年前他是我们这班“粉丝”心目中的“东邪”。他听后一时不知如何反应。我只好跟他解释说黄药师言行虽然乖僻,却身怀绝世武功。大概“武功”这句话引发他想到国藩。隔了一会他正色说:“You know what, if anyone in the field can beat me, it is Tony.” 国藩是夏公的晚辈。难得长辈对晚辈的推崇如此不惜“以身作则”。郭凡向我敬酒,说“让我们为李家干杯”。没想到这不是“找乐子”的新说法,而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著名诗歌《尤利西斯》中的一句话,在郭凡口中改成了“生命的庆典”:I cannot rest from travel; I will drink李家的生活。我一直很享受Greatly, have suffered greatly, both with those爱我的人,独自一人…Tony, Here is the Royal Salute to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