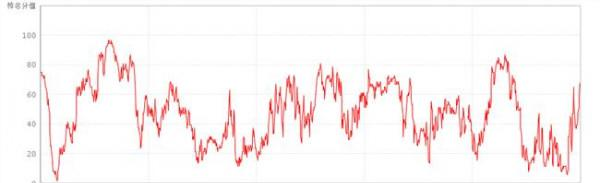公主二重唱 难以完满的现场体验 恰好证明了瓦格纳的魅力
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剧照。文中图片均来自微博@北京音乐节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瓦格纳创作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中途拐道开的一个浪漫小差。在流亡岁月之初,瓦格纳债务缠身,身体欠佳,与妻子米娜的分歧十分严重,而在此时结识了丝绸商人的年轻妻子马蒂尔德,让作曲家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成就了其歌剧创作的一座巅峰。10月11日北京音乐节上奥地利蒂罗尔音乐节带来的全新制作版本也吸引了众多外国乐迷前往朝圣。该团队将在同一周为上海观众带来一场整版的《指环》盛宴。这里也需说到保利剧院的构造并不适合演歌剧,老剧场的声学构造无论人声还是乐队都有些兜不住,声音四散漏了出去,后排观众几乎得竖起耳朵捕捉歌唱家的声音。不知同样的乐团到了音响效果优秀很多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出“指环”的时候会不会让人有更多惊喜。被视为代表20世纪初叶的特里斯坦和弦开启了听觉盛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瓦格纳达到巅峰的半音和声体系。与瓦格纳的其他作品相比,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故事非常简单,但一对宿敌男女在狂喜的作用下产生了炽烈的爱和纠缠,最终在死亡中获得了终极的安宁和解脱。在瓦格纳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浪漫主义达到了顶峰,整个音乐剧充满了热烈的爱与情,无尽的欲望,音乐充满了肉欲的挑逗和缠绵,以至于格式塔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冯·艾伦·费尔斯甚至声称,他可以通过点击特里斯坦的一段来引发听者的“高潮”。
蒂罗尔音乐节管弦乐团
如此说来虽有夸张之嫌,但曲调中严丝合缝的内部和声、半音化的处理,还有无休无止的“不解决”属七和弦的运用所造就的欲罢不能的势头,都是这部作品令人神往的魅力所在。有很多关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故事。据说有些人看剧的时候晕倒了,有些人太激动了,看不下去。据说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在听特里斯坦的时候也因为紧张而晕倒。在维也纳版本中扮演特里斯坦的阿洛伊斯·安德于1865年死于精神病院。序曲一开始就昭示了整部作品的精髓。半音上升的渴望、半音下行的悲叹,极端表达了不断渴望、不断欲求的中心意念。乐团徐缓进入,深情有余,而魅惑不足。速度推进偏快,削减了悬念和张力,序曲应有的铺衬变成了一个简单展示瓦格纳音乐风格的陈列馆。让这部作品一开始就铺展得不尽如人意。乐队放在舞台后面,在空之间占据了整个舞台的三分之二以上。它提醒观众,这是一部音乐剧,音乐永远在场,就像永远在场的瓦格纳。这个灵感值得骄傲的是,指挥古斯塔夫·库恩参考了瓦格纳关于诠释歌剧体验的原创文献,瓦格纳强调布景要易于操作,所有的制作都要适合简单的技术设计,这让所有的舞台体验都回归到音乐最基本的本质——所以在这部四个半小时的歌剧中,极简主义的布景只是舞台右侧三块白色布拉出的桅杆帆的轮廓,或者是下一个场景中左侧倾斜的木板所拯救的简单山坡。舞台的简单绝不足以成为我评价这部歌剧不尽人意的原因。毕竟,世界上有一大批瓦格纳的忠实追随者,他们讨厌拜罗伊特或大都市的天才导演,这些导演近年来在大神的威严下传授他们的技巧。所有花哨的外表和新奇的想法都不足以给伟大的音乐锦上添花。尤其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德出来的时候,人物关系简单明了,在制作上翻花头也不一定讨喜。说电影《王者之心》充满了浪漫的英雄主义和家国情怀是不现实的。然而,音乐表演的缺失不得不让人由衷地感叹。在中国很难看到令人愉快的瓦格纳。
最大的遗憾在于特里斯坦的演出者詹卢卡·赞比奇表现平平,开场温柔得如同情场失意的花花公子,哪里有一点斩杀了敌军大将的英雄气概。伊索德的女高音莫娜·索姆对瓦格纳的演唱更有经验,能控制自己的硬件状态。娇小的身材让这个角色难得一见,不让人在视觉上发挥。虽然低音区略显单薄,但在音量、穿透力、戏剧性上均优于搭档。毕竟,瓦格纳的歌剧对歌手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历史上唱死人的极端事件不在少数,当今世界能唱全剧的歌手屈指可数。第一幕中仇人见面分立舞台两侧的对唱有庄严的仪式感,伊索尔德向特里斯坦“索命”时的咄咄逼人,乐队的铿锵壮怀激烈颇为决绝,乐团调和着情绪的累积和增长。醉药,灯光渐暗,乐队拖着长音晃出躁动不安的气息,情欲在昏暗的灯光下酝酿发酵。这不像歌剧中的爱情二重唱或《爱情之死》那么出彩,但却是一个非常精髓和迷人的小片段。通常,我们习惯于称瓦格纳的歌剧为“音乐剧”。音乐和人声在瓦格纳的音乐剧中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乐队不必回避抢走歌手的风头。有时候人声只是音乐的附属品和点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接受一部歌剧如此缺乏视觉感的原因。
更大的问题暴露在第二幕中。爱情二重唱是歌剧史上男女二重唱的巅峰,两个人幽会场面,二重唱长达四五十分钟,这在音乐史上前所未见。然而在眼前上演的版本中,一位表现力尚佳的伊索尔德和一个乏善可陈的特里斯坦令这段巅峰二重唱显得散乱而力道失衡。一个穿透力强劲的女高音在挣扎呐喊,而男高音的声线光是和乐队抗衡就已经勉为其难,何况还需要表现出炽烈的荷尔蒙和内心呼唤,简直太难为这位小号威尔第男高音。如果深入表演,虽然伊索尔德并不迷人,也不躁动,但和状态不佳的特里斯坦副总裁相比,还是相当吸引人的。莫娜毕竟唱的是女武神,战国公主刚毅坚强,也是以英雄气质打败了所谓的英雄情人。但特里斯坦原本是剧中的“逆袭”角色,从第一幕的酱油王到第二幕的亲密爱分享和表达,再到第三幕重伤后完全变成了独角戏。随后,在该剧第三幕,观众意识到男主是个“诡计多端的泼妇”,他面前的温水完全是在为接下来的独角戏积蓄能量。没有对比。看到特里斯坦的辛苦表现会带来一些戏剧性。至少在这个时候,表演态度是正确的,足够敬业的。然而,意大利男高音的基础并不适合瓦格纳。唱完之后,他嗓子都哑了,声音又累又哑。而且,一旦仆人回应,男中音中的金属质感和铿锵度在听觉美感中很容易占据上风。
不过看着赞比奇的声嘶力竭也能够非常贴切地体会这个角色的难度——在亢奋与虚弱之间的转换的确是对唱功和演技的双重考验,瓦格纳没完没了的回光返照听得人过瘾,对歌唱家而言着实是种折磨。毕竟瓦格纳每每创作的初衷,也就是往耗尽演员的极限去写就,这位恶魔作曲家追求表演状态的极致,是演出者生理上的极限和戏剧人物状态的高度统一。想想看,在舞台上只靠一个演员来支撑,四十分钟到五十分钟的戏,又要达到这样的力度和表现力,即便是有音乐的辅佐依然是个体力活。特里斯坦一面要表现垂死的虚弱状态,一面要表现出生死边缘对挚爱的呼喊,不过导演难道不觉得演员肢体上全程美人鱼侧卧状实在是没有美感又不利于发声么?然而,女仆和伊索尔德的二重唱在完整性和表现上都是优越的。遗憾的是,两位女歌手的音色差别不大,都属于圆润厚实型,趋于同质化。这是说瓦格纳对歌手的选择一直都是那么有限,挑三拣四的不容易。在我的印象中,瓦格纳在一封信中不安地承认他的音乐“把歌手拖下了深渊”。
对于导演来说,简单的布景和调度几乎没给这个戏加什么分。倒是分别场面的设置颇得我心,特里斯坦最后在伊索尔德的呼唤中气若游丝地呼唤爱人的名字,枕着渐弱的弦乐,深情绵软地陷入长眠,平静地分别衔接女高音高亢的“爱之死”咏叹,起伏得恰如其分。整部歌剧结束后,虽然像是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但观众的兴奋之情更接近于完成瓦格纳作品的一次“攀登”,这在国内实属罕见。毕竟这群人是从下午五点进入剧场,在幕间休息时冲过去啃两个面包,一头扎进剧场接受“洗礼”。很多掌声都给了我经历过的那个夜晚,当我走出剧场,穿梭在耳边的讨论中时,也有不少失望。可能是瓦格纳的期待在体验上趋于“极端”,所谓热血沸腾在整部剧里只占很小的比例,偶尔会推起一个小高潮,但从来不会让人满意。
乐队的表现整体平稳,大部分时候虽不失庄重也有着很高的完成度,不知是否因为音乐厅对声音的表现力留有遗憾,但总觉得激情与细腻都不足,少有真正推得人癫狂的冲突感,或者于细节处处理出感人或惊喜的小火花。也可能因为整个配器写作中铜管发挥的空间不大,因而也没有《女武神》或者《罗恩格林》那般来得恢弘。总之,现场聆听的体验与之前关于这部剧的传说相比实在是太弱了,但第三幕开始时“爱比死更冷”的沉默多少有些让人回味。但是,既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有些勉强,也值得几声欢呼和称赞。友人说,拿现场跟那些百年奇才流芳百世的商业录音比较,不公平。种种不完满的体验也许正好证明了瓦格纳的巅峰才华和恒久魅力。何况这个班底,在演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的两天刚刚搬了一出《纽伦堡的名歌手》,而几天之后又要飞抵上海上演鸿篇巨制的《指环》,选择比较省力气的节奏,也算顾全大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