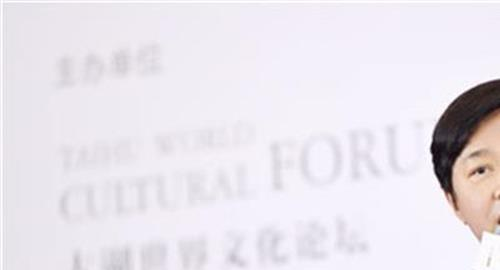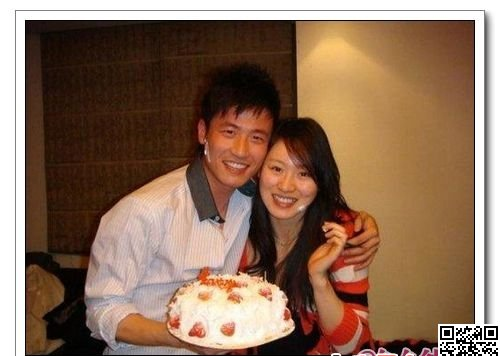潮涯 吟咏富士山的诗为什么总能被一眼认出
富士山
没有完整精神的人,看不见山水。比如在古代人眼里,山川是神,每一个风和草都是神。人只需要服从命令,不需要仰望上帝。在中世纪,蒙娜丽莎背后的风景美丽而干净,但谁看到了呢?好在这边有个陶渊明,那边有个华兹华斯,然后把手指往外头一指,说,要有山水。于是便有了山水。根据初中语文课本的完整解释,陶渊明写的山水是理想的故乡。陶谦之后,住在山川里的人兴盛起来,坐在厅堂里,躺在书房里,都唱着歌回西藏。哦,不,回到山里,照顾这个世界。王维说“松树林里的月光,小溪里的水晶石”,多么优雅,就像“朋友的王子,当你在这里的时候?”下面。想到官员面前的风景,想到生活在水,我在法庭上也是一个红人,就像硬币的正面和背面。这么想来,陶渊明让人发现了山水,却也带坏了山水。我朝风景诗处处都是人的影子,字里行间多带动词,生怕读者不知道“我在这里哦”。诗句固美,但记住的是诗和诗人,山水到底是个啥样子,还真忘了。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太行还是武夷?也很奇怪,中国地大物博,撞了太多“山”,只好将就,把不同的感受放在相似的山川里:爬这座山的时候害怕,过那条河的时候孤独,所以这座山不是另一座山,这条河也不是另一条河。这些人拿起画笔,也忍不住在山岭间添几间茅屋,在江面放一叶扁舟;或有人演孔子,在画面中春服而歌,或有人扮姜太公,在大雪天死握着钓鱼竿搞行为艺术。哪怕是五代时期擅长画全景的画家荆浩也要在长长的《匡庐图》里藏几个亭子。这叫什么,叫意境,叫追求。山水里面不藏人的痕迹,山水就是死的。藏的那人,就是创作者的灵魂附体。这也是朋友和邻居看到的。赤井良彦在《中国山水诗》中说:“钓鱼是地位低下、生活困苦的象征。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拥有批判性原则作为既定价值和伦理框架的意义。”话绕口,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放在山水中,不可能是猫和狗,一定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符号。而“渔夫”是大家都醉了,我一个人醒来的象征。放什么“人”进山水,山水就是什么精神气儿。朋友也写诗。友邦保险的中国诗歌在平安时期的宫廷和镰仓时代的佛寺。最古老的诗集是公元751年的《怀风集》。江户时代,中国诗歌蓬勃发展。不仅是汉学家,就连像西乡隆盛这样的武术家也有诗,有几千首。明治以后,袖珍版低价选诗盛行,许多编辑希望通过普及中国诗歌来对抗通俗文学。柿村重松所编的《和汉名诗类选评释》就以成为“感奋兴起之资产,移风易俗之一助”为夙愿,被重印了数十次。《评释》将日、中诗歌分成“感怀类”、“节序类”、“名胜类”等二十二类,每一首都有翻译以及简评。而“名胜类”就是中日山水诗了。此类中国诗四十首,日本汉诗六十六首,是全册数量第二的大类别。对照翻阅,可一窥中日在描写山水的异同。1898年,富冈铁斋富士山
汉诗本就源自我朝,日本以中国诗为圭臬。所以日本的山水诗同样少不了“人”。只是中国这边只有一首“无人”的诗,日本那边却有四首“无人”的诗作入选。而四首之中,就有两首是写富士山的。一首是广濑范的《富士山图》,另一首是柴野邦彦的《咏富士山》。前者曰:一座山排放东海,三座峰支撑北斗七星。在齐鲁,泰山是培训中心。竟说“泰山也不过是个小土丘罢了”,我虽知富士山三千多米,泰山不到它一半,但也不免摇了摇头。山比秀美险峻即可,比高作甚,我方可是有珠穆朗玛。可诗中既然点出“东海水”,似乎的确在东海范围内无以争锋。打油诗似的简单诗句,却实在地说出了富士山的特色。吉田版画中的富士山
《咏富士山》更是特点鲜明:谁来浇灌东海,濯玉莲。潘到三大洲,插天八叶。云蒸山麓,而太阳和月亮避开中心。独立、原创、无争议,是越宗。第一句说地点,第二句说形状,第三句说气势,第四句说地位。整首诗歌除了第三句,句句指向富士山的独有特色。尤其是“芙蓉”,正是形容富士山的专有名词。比如虎门樱田的《登芙蓉峰》有“天工削出玉莲崇,八朵齐开各竞雄”,赖山阳的《题富岳图》有“帝掬芙蓉雪,置之赤县西”,或者秋山玉山直接把题目写成《望芙蓉峰》并有“突兀五千仞,芙蓉插碧空”之句。日本有研究指出,芙蓉来自李白的《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中的“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我不懂李白为何看着华山会脑洞大开想到花,但是却可以理解为什么用芙蓉形容富士山。当你坐着电车从山脚经过,富士山的形状基本不变,既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也不是“远近高低各不同”,而是山脊无比平滑的等腰三角。富士山的线条之整齐,说它是一朵簇拥着花瓣的莲花也不为过。吟诵富士山的诗词总能一眼认出:面朝东海,春暖花开。诗人不遗余力地描述它在各个季节甚至几个小时内的样子。阚茶山用“东游的不是久游者,而是一种黑芙蓉”来形容暮色中的黑富士。在这些诗中,作者只是富士山下的一粒尘埃,无论是“有人”还是“无人”。人的感情,“隐居”的态度,完全消失。读者只记得富士山。富士山图亦如此。中国山水画一定要有人气儿,富士山图却可以只有一座山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多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图景,极富生活情趣,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作品。然而其中描绘红富士的《凯风快晴》依然简练无比,只有几何图形和大面积红色。这大概不是因为他懒,而是一贯审美使然。谷文晁的“富士山屏风”描绘了雾蒙蒙的富士山。笼罩在雾中的山峰正在逼近。对于中国画家来说,无疑是一个仙境般的隐居之地。有必要给手痒加一间小屋,在幻觉中标记自己的房产。然而,谷文晁什么也没补充。在我们看来,追求似乎太没有吸引力了。杰克画罗丝,美胸之上加了一块海洋之星,搞得后世只找钻石,唐突美人。对于日本画家而言,富士山本身就带着灵魂,自然不再需要茅屋或渔翁点缀。同时他们也不向这座山寻求什么慰藉,只埋首于表现山的特征。这真说是爱到无我,爱得深沉。写诗作画,我们都说有意境者为上品。且山水诗画的意境还得是老庄,是禅,不能是豪门宅子或者青楼女。如下雨天最配巧克力,约定俗成。然而日本那边的富士山,却既无人的视线干涉,也无人的理想追求,就是那么一个孤零零的大三角,永远不管不顾地屹立着。有我还是无我,哪一方是真的禅意,不敢妄断,只是看多了理想和姿态,偶尔吃碗不配菜的白饭,倒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