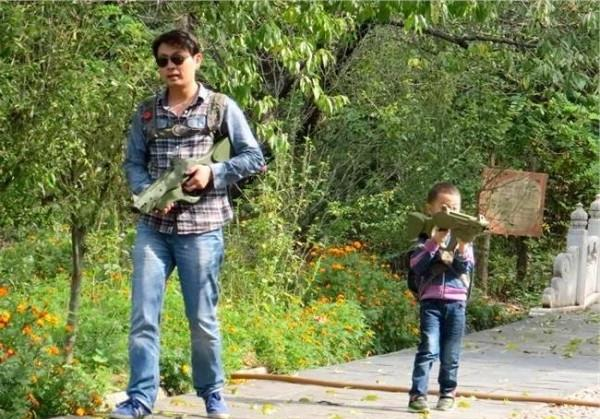凌叔华 小转铃专栏:萧然物外凌叔华
凌叔华,20世纪20年代文坛上的才女。
民国几大才女之中,萧红的天赋令人惊恐,林徽因的敬业使人敬佩,张爱玲的才能令人心疼,唯独凌叔华的文字,穿透百年时空的障蔽,和我发生隐隐的共鸣。读完她晚年写的自传体小说《古韵》,我的心被狂喜的潮水一遍又一遍地冲刷:这种含蓄、有节制、富有同情心、深藏不露的幽默感,几乎是叙事文章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她写的大部分题材都是家庭日常事务,但里面没有烟火气。传统上,大妈们嫉妒这种低俗场景大致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用狗血的情节刺激观众的消化系统,就像现在随处可见的后宫剧,或者像一些怀旧的女士一样把尴尬的场景美化成高级记忆。但凌叔华既不嫉妒也不夸张,不评判互相打架的阿姨,有着真诚温柔的同情和好奇。到目前为止,我只在加拿大人菲利普·马尔尚的《麦克卢汉传》中看到过这样的标准。这样的作品没有错,比如跳脱、活泼,或者如此大量的写出严谨精彩的情节,但并不少见。民国时期的梁遇春、废名,英国的兰姆,都是我喜欢的作家,但他们还是和凌叔华不一样,凌叔华极其爽朗温和。作家不炫耀自己的写作技巧就像猴子不挠屁股一样难。要达到凌叔华这样的境界,除了智商、情商和极其平和的心态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肯定读者的能力,要肯定读者有和他们一样的学识,这足以读懂字里行间的精妙和隐喻。“闲来静坐学垂钓,秋水秋色入画图。”这是凌叔华题在自己画上的一句诗,拿来作为她写作风格的代表,再恰当不过了。她没有写过文论,却写过画论,她说中国画所追求的“画尽意在”,她写的《古韵》却是达到了。凌叔华的一生,虽然出身清贵,寿数更长,往来皆是鸿儒,身世亦颇平顺,可作为一个作家,真正欣赏了解她的人却寥寥无几。后世提到她,八成是为了她夹在徐志摩林徽因中间的尴尬角色。因徐志摩信任她,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她保存,徐死后便为了这东西弄得满城风雨,平添了无数八卦轶闻。剩下的两成里,又有一成半是为了提她和伍尔芙的百合故事,以及和伍尔芙侄子朱利安之间的婚外恋情。只有最后半成留给文学史,却只照出一个模糊而扭曲的倒影。她虽和周作人有师生之谊,丈夫陈西滢却卷进和鲁迅的骂战中,鲁迅对她的评价也极敷衍:“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有此“高门巨族”的标签,凌叔华从此难逃中国文学史上的边缘角色,人们想到她,总觉得是深谷幽兰,思维阅历都有局限,并非大才。像柯灵之流的评论家,常爱说她写小说不够深刻,或是缺乏为人的热情。我觉得,这是因为这些评论家们本人口味太重,吃惯了湘菜和川菜,当然就吃不出粤菜清淡的好处了。这大概也是阎连科之流哗众取宠的作家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吧。她写小说,写散文,其实是类似人类学家写田野笔记的方法,虽也承认和文中角色有同生为人的情感,但更有一种清风朗月的克制和平和。对那些不写剥皮强奸就不知道该如何动笔的“主流作家”们来说,她当然是太清淡些。她既是画家,自然爱山爱水,写山写水时那种由衷的兴味,和《徐霞客游记》亦相去不多。她写人在山中,有时看前看后,为景色所迷,便会发生“山醉”、“林醉”,我常常觉得,她这一生也像是个尽兴的游客,只为种种景色所迷,却从不为之驻足,彻底驻扎下来。理解她的人极少,能欣赏得了她的人更少。她教导自己的独女,说女人绝对不要结婚,万一结了婚,绝对不要为丈夫洗内衣,更加不要向男人认错。可惜女儿对母亲的教导并不以为然,说父亲陈西滢讲原则,母亲凌叔华讲利害,言下对父亲同情多,对母亲的认同少。在回忆母亲的文章里,直承对母亲理解不多,只强调凌叔华的高雅,没有提到她的大气、诚挚和天真。回过头来想想,凌叔华实在是个再现代不过的女性,只不过因身世清贵,格调高古,于世事也不如典型的艺术家一样笨拙唐突,就被贴上了传统婉顺的标签,实在是冤枉得很啊。不过,想来她自己也并不介意吧,她临终前回到故土北京,看着熟悉的北海白塔,所叹也不过是山河之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