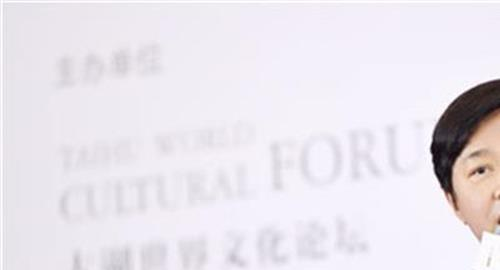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汪曾祺女儿谈父亲:他知道自己会在文学史上会留下一笔
汪曾祺
“实际上,他这个人还是有一点狂气的,喝点酒爱瞎说两句,说文学史上他会留下一笔,我们都笑他,没拿他当回事。”1974年,汪曾祺去呼伦贝尔草原体验生活,作家兴安的父亲负责接待。12岁的兴安第一次见到汪曾祺。第二天,晚饭后,一群人去看大草原。那是六月。黄色的花覆盖了草原,几乎所有的绿草都被黄色的花海覆盖。汪曾祺做了一首打油诗:“草原上的花真美,像韭菜炒鸡蛋。”大家都笑了。 “起初我觉得这叫什么诗呀,后来一琢磨,黄花配绿草,跟韭菜炒鸡蛋的感觉真是像,汪老在诙谐当中将触目所及的草原极生动地传达了出来。”5月29日,值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小说全编》之际,兴安在故宫西华书房举办的文化沙龙上介绍第一次与汪曾祺接触的情景。汪曾祺小说全集封面。
《汪曾祺小说全编》收入180多部小说,是迄今为止对于汪曾祺小说搜罗最为完备的集子,比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的汪曾祺全集增加了27篇。人文社方面介绍:“其中24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汪曾祺小说创作起步于西南联大,他的老师沈从文对其创作的影响很大。汪曾祺民国时期的小说,如《崔子》《楚年》《灯下》《最响的鞭炮》《驴》等。,在新增加的24部早期小说中,都是全面发展的短篇作品。它与20世纪40年代写的著名名篇如《名鸡名鸭》《老鲁》《落魄》等品质相当,并不逊色于后来为他赢得文学声誉的《天启》《大闹年谱》。新增小说27部,有近年来学者发现提供的,也有王先生家人发现的。比如《葡萄上的轻粉》《锁匠之死》《八宝辣酱》在第一派、第二派甚至通读的时候就被发现了。"被称为“中国当代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的汪曾祺自1940年开始文学生涯,在小说、散文、戏剧创作领域皆有成就。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知道他的人并不多。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刘树勇在《在江湖》一书中写道:“大学毕业时,我写了一篇论文。当时看了几部汪曾祺的小说,和当时那些作家写的完全不一样。确定题目后,我问教当代文学的老师怎么写。结果,老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作家。他还说,其他老师不知道作者是谁,也不写别人。”市井小说“感觉如玉”作家阿城说,汪曾祺是“一个早出晚归乘宇宙飞船的哥哥”,“只有世俗的眼光,没有工农兵的精神”。阿城第一次读《使徒》时,觉得这篇文章“摸起来像玉”。刘树勇说:“‘感觉像玉’,真的很到位...我太喜欢他的东西了。我没有当时作家的粗鲁,这是非常严重的,很难表现出什么历史责任。即使谈论‘文化大革命’也是轻描淡写,似乎很享受张家口固原农业研究所无人负责的时光。每天都和那个时候不一样。文学评论家王干在沙龙上说:“汪曾祺写的市井满是诗意。写乡土、写乡村、写山水容易写出诗意,但是市井写出诗意很难,譬如《水浒传》。但是汪曾祺写的也是社会,但是他有诗意,有韵味。我们的文学史家与评论家老觉得市井是一个庸俗的、边缘的介质,随着我们城市化进程,农民是慢慢在减少的,我们都是市井中人,所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汪曾祺先生的价值会越来越体现。”兴安认为:“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属于文人小说。他写的市井小说,不一定是写给市井百姓的,而是写给相对文人的。大部分人都说第一次看什么都看不到,要仔细分析。此外,王老写现代汉语在那个时代如此纯粹和纯粹,很少能不受那个意识形态的政治干扰。”汪曾祺的女儿汪超。
汪曾祺之子汪朗。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沙龙里汪曾祺先生的女儿汪超这样评价父亲:“其实这个人还是有点疯疯癫癫的,只是我们家真的没有立足之地。他喝了点酒后喜欢胡说八道。他总是说文学史上会留下一笔。我们都嘲笑他,没把他当回事。”汪曾祺的自我和女儿眼中的“狂气”在其文章中也有所反映,如他的作品《人间草木》中所收的《夏天》:“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令人读来痛快淋漓。当谈到汪曾祺时,他作为美食家的地位经常受到关注。他的孙女汪卉在《“名门之后”个中味》中写道:“有美食家之誉的爷爷厨艺其实算不得过人,只是对各色菜品‘背后的故事’知之甚详,总能在文章中将口腹之欲联系上几分文化内涵,让人食欲大动的同时亦得精神餍足之感,久而久之竟为汪府的‘家宴’闯出一番名头,至今老家高邮仍有餐馆以此为噱头招揽生意。这位在西南联大穿过‘开裆裤’,辗转京沪落魄到有意轻生,当过‘右派’戴过帽子,种过葡萄画过土豆的爷爷,对于美食虽有追求之热情,却无讲究之矫情。街角小馆的一碟毛豆、路边菜摊的几把香椿,都可以让他眯起老眼,美美咂摸许久。”北京出版社原编辑张守仁在《汪曾祺我知道》一书中说:“即使是萝卜白菜,王老写得也很棒。我曾经编辑发行过他的一篇散文《萝卜》。他谈到高邮老家的华阳萝卜和萝卜丝饼有多好吃,北京人用萝卜片炒羊肉汤有多好吃。说天津人吃萝卜喝热茶是当地的习俗。写在四川沙汀写的小说《淘金记》里,邢默每天吵吵闹闹,用牙齿和骨头煮白萝卜,让家人的脸又亮又亮。我还提到,爱伦堡小说中的几位艺术家吃萝卜黄油,喝伏特加,风味独特。” 刘树勇最后还是决定写汪曾祺,老师没办法也答应了,但表示不了解这位作家,恐怕指导不了,刘就跑去北京找了汪曾祺。后来,在杂志上,刘树勇看到了更多汪曾祺的小说和文章。“旧的东西多说,但没有东西向别人炫耀或怀念旧的东西。只是日常情况随意而来,没有惊喜,也没有仇恨。所谓的悲喜被冲淡到了极点。看他说的世俗的东西,连腌菜萝卜怎么做都好吃。今天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气质?”刘树勇在《江湖》中写道。史航曾说:“‘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这两句诗是马一浮的,我读了就喜欢,常常提起。现在要写汪曾祺了,才发现,这十个字是应该专门用在他身上的。” 王干,江苏人,与汪曾祺交朋友多年。他曾经享受过汪曾祺安排儿子王朗为他们准备饭菜的待遇,还和老人聊起了文学。他介绍:“汪曾祺开拓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延续了五四文学的传统。此外,汪曾祺虽然用白话文写作,但他的小说和散文却具有唐诗、宋词、官至、清代和图的魅力。他还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联系起来。”指出:“王先生的早期小说是现代主义的,非常时尚。但后来,他关注的不是外国小说的形式,而是人,表现出对人的同情。他还开启了中西文学。” “另外汪曾祺把民间文学和我们所谓的文人文学打通了。汪曾祺在‘反右’期间被下放到乡下接触了大量的民间文学。所以刚才兴安说到韭菜炒鸡蛋,这个就是民间文化。所以汪先生是把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打通了。”王干说。兴安又说:“小说和散文也有联系。”“王先生的很多小说都采用了散文式的风格,不注重外在的情节,而是注重在语言之下给人一些空白,给人一些空” “汪曾祺先生小说和散文做到了南北打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杨早介绍,“作家中,很多南方人就写南方,北方人写北方。汪曾祺从高邮出来,到昆明,再北上北京、张家口转了一圈以后,对整个中国把握得比较深。尽管中国南北各省之间差异非常大,但是无论从文明、口味,甚至到方言上,汪老都能够做到拿来主义。”“这种从王老到当代文学史表层的开放,已经发生了。”杨早介绍了一则轶事作为证据。1982年出版后,《使徒行传》传遍全国。一个公社晚上开了个会,第二天清理会场的时候,发现两个农村干部正在桌布上写小英子和临海的对话。那部小说讲的是一个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实际上留在了80年代农村干部的心里。他们可以在会议中记忆和娱乐自己。这说明在王老出现的时候,打通的质量已经显现出来了。5月29日,汪曾祺小说文化论坛召开。
“大器晚成,多年陈酿”“我年轻的时候写得很快,现在已经变得很容易了。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很容易,我现在可能做不到。”汪曾祺晚年的言论给杨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进一步解释说:“汪曾祺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追求。他年轻的时候探索过无限可能,后来他找到了自己最舒服的表达方式。这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最新出的汪曾祺小说全集,上册收集汪曾祺1949年之前的小说,中下册是1949年之后的小说。恰恰这个分野构成了汪曾祺多重角色。”杨早介绍,“我觉得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曹雪芹,在第一本的时候是大观园里的一分子,他是京派最后的余韵,他是曾经在民国文学的文脉当中活跃的一个人。到了1980年代,他的同龄人,他的前辈,基本上都不写了。这个时候汪曾祺异军突起,大部分作品写过去的世界。这时他身份由大观园的一分子转变为住在西山黄叶村开始回顾当年繁华梦的时代记录者。”“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张爱玲,出名要早。还有一个作家是属于晚熟的明星型作家,汪曾祺就是后者。”王干认为,有一种像流星一样的作家,比如萧红。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文坛上,但她是一位光芒四射、广受欢迎的作家。她出来后,人们觉得很耀眼,很惊艳。另一种作家是明星作家。你第一眼看他的时候,不是特别亮眼,也不是特别抢眼,但是过了十几二十年,作家还在,三十年了,他还在写。 “也不是说作家活得越长就一定写得越好,比如萧红,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萧红活下来可能变成第二个丁玲。有一些作家是能够保持一个恒星的状态,有些作家就是一个流星的状态。汪曾祺先生属于大器晚成,他有一本小说集叫《晚观花集》也有这样的意味。”王干介绍,“汪曾祺刚出道就赶上‘反右’、解放战争等等,他的能量被积压下来,通过发酵,变成陈酿,所以越写越好。”当天的沙龙在故宫西门附近举行。刘树勇跑到北京找汪曾祺时,“没想到是个小老头。看到我小时候找他,真是太好了。”汪曾祺告诉刘树勇,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在故宫住过一段时间。晚上,他一个人呆在午门,看着蝙蝠飞来飞去,想象自己是李三,北京姜阳贼的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