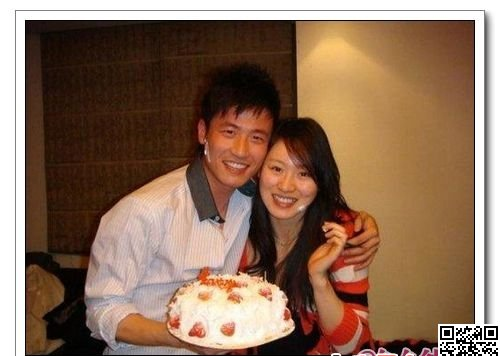巴耶克 摄影 到底何去何从 昆汀·巴耶克对谈菲利浦·盖夫特
原创 Quentin Bajac 影艺家
现代艺术博物馆,1938年
摄影正日渐成为艺术界越来越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摄影专题类的展览、出版物和艺博会与日俱增。同时,这一媒介也正经历着某种身份危机。摄影可以保持它自身的媒介性吗?还是应该被现代博物馆瞄准的更宽广的多媒体世界吞噬?关于艺术领域中摄影究竟处在何处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众多相互对峙的观点。摄影评论家菲利普·格夫特与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馆长昆汀·巴切克进行了一次对话。此次访谈的时间是2013年,巴耶克刚担任MoMA摄影部策展人,距今已过去7年,现在,我们重读此文,或许仍能带来不少启发与深思。昆汀·巴切克,2013年8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来自摄影审判席的长远之计对话|昆汀·巴切克×菲利普·格夫特翻译 | 殷洁菲利普·格夫特:你坐的摄影法庭是一个传奇的遗产。在你之前的四个人,每一个都很有名,博蒙特·纽荷尔、爱德华·史泰钦、约翰·萨考斯基和彼得·加拉西,你是否感到畏惧和挑战?昆汀·巴耶克:或许两者都有一点。您指的“摄影审判席”是19世纪80年代克里斯托夫· 菲利普斯讨论MoMA在摄影界的角色一文中用到这一词,但那已是30年前了。如今,MoMA只是众多审判席位中的一个,现在还有其他主要机构专注于摄影研究。MoMA在摄影方面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它的特色。当我们写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摄影史时,其他人或组织也在写同一时期的历史。菲利浦·盖夫特:您是否认为20世纪撰写的摄影史是以美国或者说纽约为中心?如果确实如此,这一现象近来有所改变么?昆汀·巴杰克:是的。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人倾向于将摄影视为属于美国的媒介。有点像爵士乐——这是美国艺术。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您回顾MoMA的摄影史,斯泰肯已经引入了欧洲摄影师,博蒙特·纽霍尔也是如此,花费了大量时间深耕欧洲摄影史。约翰·萨考斯基当然是一位出色的策展人,我认为任何一位史学家都受益于他的研究。但是,你知道,他特别关注美国。如果回顾他在博物馆30年任职期间策划的展览,即使有非美国摄影师的作品,也往往局限于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布拉塞特、卡蒂埃·布列松、拉提格和阿杰,他们的作品都是重复的。他也展出过一些日本摄影师的作品,但数量不多。说到当代摄影,当时他那一代的摄影师都是美国人。《镜子和窗户》,现代艺术博物馆,1978年
菲利浦·盖夫特:在确认由您担任这一职位之前,MoMA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人选。从您的背景和您对摄影的理解来看,您认为是什么促使博物馆在众多候选人当中,确信让您担此重任?昆汀·巴杰克:也许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或许他们已经感受到摄影越来越全球化,一些与摄影悠久历史无关的非美国摄影师现在得到了更合理的对待。当然,这是他们问我是否会考虑这个职位时,我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博士学位,也不是美国摄影师。我以前没想到他们会考虑采用非美国的策展人,但也许他们想修改这段历史。菲利浦·盖夫特:您在蓬皮杜任职期间策划的展览中,您认为哪一场展览对MoMA有着特别的意义?昆汀·巴切克:我计划的关于超现实主义的展览非常重要,因为它展示了两种媒体:摄影和电影。我经常研究摄影和另一种媒介的相关性,我认为这很重要。长期以来,蓬皮杜有举办跨部门、多学科视角展览的传统。我在奥赛博物馆的时候,也策划了很多展览,讨论摄影与其他媒介——电影、绘画、雕塑的关系。我认为这些对于MoMA来说非常重要,MoMA正在尝试在各个部门和学科之间建立更多的对话。2010年在温特图尔摄影博物馆举办的“图像的颠覆:超现实主义、摄影和电影”展览。该展览由昆汀·巴耶克、克莱蒙·谢鲁、纪尧姆·普法、菲利普-阿兰·米肖和米歇尔·波维尔特共同策划,于2009年首次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照片:克里斯蒂安·施韦格尔
菲利浦·盖夫特:博物馆对媒介间的“相互授粉”十分感兴趣,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特别是在艺术世界当前这一时刻,多媒体被同时运用于不同的平台上。很明显,当代艺术博物馆必须要在这场进化中进行争夺。但我很好奇摄影在这之中将如何继续?过去的四十年里,证明摄影是众多学科之中一种可行的艺术形式的战争,可以说是一路胜仗。博物馆想要将摄影的自治性剥夺走么?昆汀·巴切克: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摄影当然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这场战争已经结束并取得了胜利。我们可以对摄影的力量有很大的信心,它可以与其他技术竞争,而不用试图证明它的身份。菲利浦·盖夫特:由于在过去十二年间,新的实践和包括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内的新型平台的出现,评估一件艺术作品时的标准——是传统纪实类摄影还是构造出的影像——都要产生改变。您个人的标准产生了变化吗?比如,您如何将艺术家从实践中隔离出来?昆汀·巴切克:各种实践已经改变。目前,摄影策展人和摄影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是图像的扩散。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初,策展人专注于提供观看视频作品的机会。现在我们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太多的图像。所以我们需要非常有选择性。我认为,当前对我们策展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这片图片的汪洋中教育和引导大众。有点像拥有了来自全世界的图书,而常常更好的是读透一本书。比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位受教育程度极高的学者或许终其一生可以掌握60、70或者80本书的内容。他们或许对世界拥有甚为清晰的观察,因为他们可以专注地思考他们所看到和所读到的东西。有时真的是少即是多。我不是说一定,但通常专注于“少”,就够了。“图像的海洋”,现代艺术博物馆
菲利浦·盖夫特:那么,您的策展项目将如何推动MoMA摄影部在这浩瀚的影像大海中前进?昆汀·巴切克:我可以确认的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现在提供了艺术史和文化史,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也许我们不仅要关注艺术,还要关注文化现象。例如,我们可以建立高低之间的联系。在摄影部,我认为我们需要策划更多主题性展览,不仅仅是艺术方面,而是更广泛的文化方面的展览,这是一个细微的不同,一个更加宽泛的方法。当然,摄影专题展还要继续举办,但不仅仅专注于这一种展览,这真的很重要。我们之前也有些忽视了策划年轻艺术家的专题,那些正接近30岁或30岁出头的艺术家。博物馆的年度展览“新摄影”是为新兴摄影师举办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新的实践,我确实希望能为此注入新的活力,改变它的节奏,将每年一次变成两年一次,但是规模将比现在大很多。这一改变将从2015年“新摄影”展三十周年时开始。“新摄影”,现代艺术博物馆
菲利浦·盖夫特:我刚才看到,摄影画廊楼下现在的常设装置,艾伦·塞库拉和斯蒂芬·肖尔各占一墙。塞库拉的作品表现的是服务于社会经济文化批评的一系列观点。肖尔从一些不同的观念性的理念出发,关注影像中蕴含的可感知的特性。我在想您对差别是否有所思考,而是意识形态和感知之间的差别。昆汀·巴杰克:我同意你所说的。摄影是一种对世界的感知,即使对于在工作室工作的摄影师来说也是如此。但是让我们专注于我们所说的描述性或纪实摄影。最有趣的摄影师是那些试图在洞察力和概念之间找到正确平衡的人。几周前,我与保罗·格雷厄姆也谈到这些。他当时说,你可以设想最有可能实现的想法,打开门走到外面,然后世界会改变你的想法。你必须接受,然后调整你的期待,去适应你所观察到的,再进而就此延伸。你的最终创作或许与你最初的想法大相径庭,这就是摄影。它意味着最初拥有一个想法,接受你将被即将邂逅的世界引诱。一些摄影师十分顽固僵化,他们拥有一个想法,就只想表现出这个想法。然后还有相反的一派:没有任何预想观点就走出去拍摄,之后再试图将迷一样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根据捕捉到的图像进行构想,摄影自始便属于这一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斯蒂芬·肖尔
菲利浦·盖夫特:您是如何接触摄影的?之前也拍照片或绘画吗?昆汀·巴切克:我以前画画。我画得不多。现在我偶尔画画。我大学的时候没有学艺术。很多年前,我在巴黎的第一份工作是交流,但没过多久,我就决定必须改变,通过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来谋生,于是我向一所培训策展人的法国学校——国家文化遗产研究所申请,这所学校采用了非常正规的法国集中教育制度。我当时对20世纪的摄影和艺术感兴趣。那些让我入迷的照片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科学影像,比如埃德沃德·迈布里奇的作品。这类材料显然对现代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刚开始在奥赛博物馆任职时,远不是一位摄影学专家。我是在打开一箱箱作品,探索、审视那些作品,与影像和物体建立联系的过程中不断学习的,这也是博物馆的意义——影像是物体,它是有形存在的。这是我如何成为了一位研究19世纪摄影的专家,尽管我对当代摄影也非常感兴趣。纽约现代美术馆
菲利浦·盖夫特:您是否认为对摄影的叙述——到目前为止所被撰写、修订和改写过的摄影史——也应该拓宽思路,将摄影与电影、摄影与其他领域都联系在一起?昆汀·巴杰克:我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我们应该拓宽摄影史的叙述,这也是我在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任职期间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研究摄影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系:绘画,当然还有建筑、电影等。跨学科研究会帮我们避免将摄影史作为一个特别的艺术形式对待,我把这称为摄影史的“石化”,与此同时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与当下各种艺术实践同步的研究方法。菲利普·格夫特:你刚刚提到了改进“新摄影”展览的想法,但是你现在知道你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第一个展览的主题是什么吗?昆汀·巴耶克:一切都还未决。或许这场展览将与科学实践相关。明年2月,我会筹备以新的方式陈列馆内的永久藏品,每年我们都会改变摄影厅的陈列,我会围绕工作室策划一些内容——一种摄影师和艺术家通过摄影去研究工作室空间的方式,他们将工作室作为游乐场、实验室、剧院或摄影棚。我们会使用包括19世纪和20世纪在内的材料,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布置一些视频和影片。偷窥、监视和摄影
菲利浦·盖夫特:关于摄影的体裁,我们顺着肖像、风景或街头摄影这样的分类看下去,目前是不是还有未得到认定和归类的体裁呢?比如,社交媒体摄影或监视摄影?昆汀·巴切克:它可能存在。事实上,从新流派出现到被艺术家、摄影师、学术机构、画廊和历史学家认可和钦佩的时间正在缩短。我甚至觉得你提到的一些类型——至少是监控摄影——已经成为艺术界的一部分。我们还记得不久前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题为“偷窥、监视和摄影”的展览。相反,有一个类别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称之为“主流摄影”。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它,你每天都会看到它,但你不会在照片库中研究它。菲利浦·盖夫特:说到这点,那么将摄影书作为一个独立的体裁呢?昆汀·巴切克:现在人们正在回归书籍的形式。收藏家们收集的是照片,而不是印刷的照片。这是互联网造成的,其实今天你可以方便快捷的发布自己的相册。很多有才华的年轻摄影师不找美术馆或展览空,而是更喜欢自己编辑作品。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不断变化的摄影形式。您可能还会看到,我们正在回归小尺寸图像,因为我们都在使用iPhone。下一代会解读这些小尺寸的图像,但我还不会。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史
菲利浦·盖夫特:当然就像每天世界上都在产生无数糟糕的图像一样,也有很多糟糕的摄影图书出现。这并不会使已经得到出版的优秀书籍大打折扣,只是有了更多让你挠头的作品。我一直在思考马丁·帕尔出版的两卷本世界摄影书史非常出色。书的形式会成为您在摄影部研究某个首要目标时的一个考虑因素么?同样,网络呢?昆汀·巴切克:我认为我们应该出版更多的书,包括更多博物馆收藏的作品,因为最近的一本关于收藏的书是根据约翰·萨克斯在1990年写的《摄影到目前为止》,那是在摄影发明150周年之际。我认为我们应该计划出版一套两三卷的摄影作品,我们应该让尽可能多的收藏品出现在互联网上。我希望在四五年内,所有的收藏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看。菲利浦·盖夫特:这真是让大家都可以获得的极为重要的资源!也是让馆藏作品民主化的一个方式。最后一个问题:您之前的几位策展人的作为各有千秋,您对形成您的个人烙印有什么期待?昆汀·巴切克:让摄影系及其藏品更好地与馆内其他藏品融合,与其他部门有更多的对话,有更多的国际视野。-- end --作者菲利普·盖夫特,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超过 15 年,曾经担任的职务包括头版图片编辑和文化版块的资深图片编辑。2010 年,他担任制片人制作了屡获殊荣的纪录片《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他曾获盖蒂研究中心的博物馆驻留奖金,着有《弗兰克之后的摄影》等书。翻译者殷洁,艺术史与摄影爱好者,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工作、生活于巴塞罗那。/世界摄影史/本课程将基于三个方面:第一,厘清世界摄影史的脉络;第二,阐明世界摄影史发展的内在原因;第三,尝试建立自己的摄影认知体系。
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依次深入及平行展开,摄影师不仅可以了解摄影的发展历程,还可以较清晰地认识自身所处的摄影地位,从而为进一步欣赏、拍摄作品打下坚实基础。摄影史是艺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摄影史家根据艺术史的一般原理,将摄影与艺术史分开,形成一个特殊的范畴。随着摄影的不断发展,摄影史的内容也在不断拓展,使得摄影与艺术的交融变得更加紧密。当代摄影不仅是摄影史,也是当代艺术史,这使得摄影的身份变得复杂而多义。如果溯源而上,从摄影诞生之时起,摄影就已经将成为艺术作为己任,以一种若即若离地状态参与、观察、见证了近现代艺术史的发展。曾经,艺术史学家和摄影历史学家试图将摄影和艺术史分开,但现在这样的努力似乎有点徒劳。摄影已成为当代艺术,并在其自身建构中产生了审美价值和哲学体系。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发现并观察到了我们认为已经以极大的兴趣了解了很久的摄影。主讲人:戴菲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青年学者;馆长。曾多次在平遥、大理、丽水、纽约摄影节及画廊群展、个展中担任策展人、艺术指导;获各类展览、比赛、理论研讨会等奖项;发表专业类论文及艺术评论文章数十篇,出版有摄影类着作十本。原标题:“摄影,何去何从?|昆汀·巴切克谈菲利普·格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