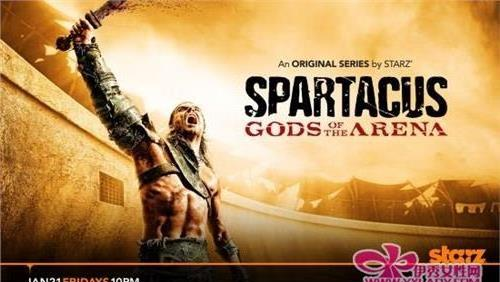白村江战役 争论与启示:白江之战是否颠覆了东亚历史
文
唐高宗龙朔三年的白江之战,在日本学术界被称为白村河之战。战斗地点在被唐军和新罗摧毁的百济故地,即当时被唐朝囚禁的金雄都督府辖区内。一般认为,具体战场在白江入海口附近。交战双方主要是唐朝和日本。新罗军和百济复兴军是否直接参战,至今仍有争议。除此之外,学术界对白江之战以及东亚国家间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也是争论不断,讨论也依然很多空。近日,日本文化教育教育厅中村丰臣秀吉教授就相关问题提出了许多“颠覆性”的观点。本书受众面广,内容全面涉及天志在《日本国志》中记载的文献考证和学界各种代表性观点,不容忽视。
为什么这场战争席卷了东亚
隋唐时期,只有“辽东不客”,杨迪多次远征失败。唐太宗和高宗复兴了“辽东之战”,他们从辽东和登来作战,海陆并进,但没有攻克高句丽的都城。新罗支持唐朝,对抗高句丽、百济、日本组成的“联盟”。自南朝以来,日本通过百济吸收了大陆的先进文化,两者的关系密切而持久。在新罗的推动和唐朝内部战略调整下,以先平定百济再自北向南攻打高句丽为目标的“百济之战”被提上日程,并迅速取得成效。百济卒于唐五年。这就是三年后爆发的白江战役的国际背景。
在白江之战中,日本为什么要倾巢而出?或者说,百济灭亡后,日本为什么要帮助百济残余势力复兴国家?这两个问题是理解白江战役爆发的根本。《天志》以“白村河之战”为题开篇,从日本朝廷的角度进行论证,针对学界以往的研究:第一,白江之战中出动的日军究竟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军事力量,还是一名国兵?第二,日本以护送百济太子回国为名派出军队。顽固的王子杀死了雇佣兵将军后,他应该撤军。参加白江战役而不退兵的原因是什么?
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很明显“白江之战绝不是一场简单的局部战役,必须放在唐朝的东北管理和半岛战略中来评价”。唐朝出动陆海军歼灭百济,建立了金雄、东明等五府尹制度。在作者的解释中,这些只是王室的灭亡,而不是整个百济国的灭亡。因此,继承亲唐孝德天皇的祁鸣皇帝,在面临百济复兴势力的帮助时,决定与唐朝作战。当时百济反唐复兴军一度占据优势,唐朝对高句丽的战争前景仍不明朗。日本及时参战,不得不阻止大唐控制朝鲜半岛,染指岛屿。老齐明来到九州监督战争,但在战争开始前,女皇帝去世,继承皇位的大兄弟仍有机会退出战争,但年轻的新君主坚持派出三支军队。我们认为,日本皇朝基于其在朝鲜半岛的既得利益,即与百济的政治文化联系,毅然不断出兵,坚持参与与唐朝的直接对抗。
因此,第一个问题很容易理解。中村修也通过仔细分析《日本史书》中的军事记载,驳斥了白江战败是兵力不足的观点,认为日本三次出兵约4.2万人。他在这里引用了森喜朗公章《白村河后》的观点,弥补了井上弘之和铃木敬民对后续部队人数统计的不足。重点在于富玉王子回到百济故地谋杀鬼房祈福后,天智追击“万余运动员”。问题是当初是福将援军转移到日本,帮工没了,申请者也不知道。然而,日本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再次增兵,这意味着白江口决战并不是一些学者提出的遭遇战。值得注意的是,提交人并没有止步于森喜朗公章的统计,而是进一步驳斥了他的观点,即并非所有实际参与的部队都派出了部队,并得出结论,所有的日军都是在百济亲王的指挥下集结的。可以看出,此时百济的反唐复国运动,本质上是日本兵与唐军的较量。
这两个问题虽然各有其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反驳了日本学术界关于白江之战失利纯属军事失利的说法,认为这是日本朝廷应对东亚局势变化的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接近事实。
日本变成监狱了吗
《天志》一书颇具颠覆性,它以史料分析和推论的方式,提出了与以往中日韩学者不同的见解。第一,日本战败后,并不是史书记载和学者说他们逃脱了唐朝的追捕,而是曾经建立了和百济、高句丽、新罗一样的关押制度。其次,遍布日本中西部的朝鲜山城并不是为了抵御战后唐军的进攻而修建的,而是唐朝统治时期便利的交通设施。
根据逃出日本史书的船员记录,作者推测,白江之战日本几乎全军覆没,没有一个将领幸免,这是事实。后来,他驳斥了森的观点,即战后日本最紧迫的任务是整顿防务,以应对唐、新罗联军的进攻,并否认了钟江洪的观点,即日本正在建设大寨府作为对抗的据点。事实上,这两位学者的观点代表了日本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防御的典型代表是朝鲜山城。作者是针锋相对的,他的论述暗示着,已经失去全军力量的日本,已经没有时间、动机和必要去建造一座城市来迎接战争。
仓本弘树声称,“取第12名”是天皇和大臣们加强战时制度的一项举措。相反,作者对取第12名的解释是为了重组战时统治,选拔对战后外交有贡献的官员而进行的人事变动。作者一方面用新出版的墓志铭纠正了池内广司的错误,另一方面肯定了铃木敬民认为后者是后人对史料的润色的论断,但强调郭吴军和你的军队,都是唐朝的附会百济人,去日本代表胜利的一方,是金雄巡抚公署派来的。新藏人政道认为,此时日本不可能高调拒绝郭入京。笔者进一步认为,当时的日本宫廷在郭吴迅一行下榻的金纳宫,编纂史书的天平时代重新诠释了奈良时代的国际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曲解”。第二年刘作为大唐朝廷的官方使者前往日本,而不是直接派出的使者,也未能进京,这一事实就是证明——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了易敏仪的证实——而数次前往日本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追究责任,要求战争赔偿而被田村元成否认,而弘提出的孤立高句丽,对于明知日军主力已被歼灭的刘来说,是没有必要的,也是难以成立的。
进而推测,唐朝不仅在百济、高句丽成功实施羁绊统治,还采取了同样的称霸日本的方式,即《日本国志·天志》六年篇中出现了“筑紫都府”。八木冲的代表观点是,这是对史料的误读,应该是属于日本朝廷的“筑紫戮”,而不是唐代的“筑紫巡抚府”。相反,笔者的观点是,《筑紫都府》不是错误,而是反映了后世编纂者没有删除的残真。在这一点上,笔者参考了唐代五都府继承了百济旧五大建筑的观点,认为日本保留了大寨作为都府的继承者,都府是在刘访日时设立的。
西固认为这一时期日本修建的朝鲜山城就是百济山城。笹川解释说,这是抵御唐朝和新罗进攻的产物。作者根据山地城市多分布在内陆地区而不是西部沿海地区的特点,驳斥了这一理论的不合理性。通过分析大部分建筑者都是百济人的事实,提出只有唐朝才能指挥百济人大规模建造城市。《史记》记载是大和朝廷下令的,至今仍是后人打磨的历史文字。但是,唐朝在日本修建山城的目的,却与阻止大陆势力从北方入侵的俗语相悖,而是考虑到九州的强大势力从南方进攻吉吉都都府要塞而修建的,还被作为据点,将吉吉的统治推向整个九州岛。这与龚楚·尚德等学者敏锐发现的朝鲜山城郭珊式防御弱点相呼应,并通过在高地构筑外力监视当地抵抗力量的功能加以解决。鉴于考古学家明石良彦将小野城的建造技术与百济府苏山城的建造技术进行了比较,且其附属仓库大多建于奈良时代之后的理解,笔者针对唐朝军队很快就撤离日本,山城被搁置后被日本朝廷利用建造。一些所谓的山城,如对马岛上的金田市,作者认为与其说是防御设施,不如说是便于与朝鲜半岛联系的篝火设施。
针对吉田孝的代表观点——日本不仅在各地修建了朝鲜式的山城,还将都城迁到水军攻不下的江边,以防备唐罗俊——笔者列举了几个理由予以全盘否定:一是日军没有那么多兵力充实山城防御,被彻底歼灭的日本坚持备战;第二,山城的点状防守态势在战略上并不构成防守链,唐骏完全可以避开山城,一路追击。钟江洪认为山城是百济人修建的临时避难所的观点,也遭到了笔者的反驳。主要原因是防御战都是以自己部队的救援为基础,这些山城显然无法坚持到敌军突破,这一点从考古研究的角度得到了明石吉彦的支持。根据史料,笔者认为朝鲜山城实际上是朝鲜半岛通过唐朝金雄府与日本之间的交通工具,是日本统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唐朝第二年,高宗皇帝在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仪式,这是帝国最重要的盛大仪式,象征着帝国繁荣的辉煌时代的到来。除了来自唐朝周边突厥、于阗、波斯、天竺等国的大臣及其代表外,来自新罗、百济、塔罗、日本、高句丽五个东亚国家的使节也无一例外地参加了仪式。然而,对于日本使臣在历山参加百济新罗血盟仪式后是否随唐朝将领漂至海西,笔者以刘仁元、刘的论证推翻了池内洪的肯定观点。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证明日本使臣不是铃木敬民,郑晓云认为他们是白江战役中战败的守备石头。守备石的职责仅限于去历山盟,相当于战败。作者被推定为高句丽使者傅南亲王身份的“酋长”,因此候选人被锁定在除天智皇帝之外的海人亲王或犹大亲王。根据《淮风藻》中对犹大王子面部风格的描述等证据,他很可能是九里山任务的领导者,然后去泰山参加禅宗。显然,作者勾勒的泰山禅宗图景,是以大唐帝国统治的东欧和亚洲为背景,包括东亚国家。
论证与启示
天智提供的历史认知是有限的,不能完全理解为历史真理,但其启示是无限的。这里还有一个例子。过去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学术界强调东亚吸收了唐朝的法律和文化。笔者在对桂头清明、铃木敬民等学者分析的基础上,再次强调日本的“近江令”及其法律制度不仅来源于唐朝,也来源于新罗。由于战胜者和战败者的结局不同,新罗保留了更多的贵族权利,法律的执行也不完整。但日本深受法制影响,最终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大宝律》,整本书从破史书整封到史料考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学者的描述和见解被一一得出,客观上有利于拆解前学术史的积累,不断怀疑古人和今人。对于长期沉浸在东亚历史领域的专业学者来说,打破思维定式,开始将目光转向具有学术确定性的历史理解,也是有帮助的。首先,这样的质疑值得提倡。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许多论述并没有可实施的结论。事实上,就目前的史料而言,他与学术界争论的许多问题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比如铃木敬民认为,芋头与白江之战有关。参议员关公等人还说,太郎与百济站在同一战线,与唐罗联军作战。但笔者以小国之利为由,认为芋头没有必要参加对唐之战,并反对“傅、钟繇等”的反证,决定予以否定。,领导了学者和妇女以及日本人民,并一时失去了国家”。另一个反证是,史书上记载,太郎曾派三位使节出使日本。首先,作者声称这只是单方面的特使,然后说日本可能会派使者与太郎交换信息,前后令人费解。然后,作者将《日本国志》中没有记载日本出使芋头的原因归结为隐瞒与唐朝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那种“刻意剪裁史料”,而是“极力白万史料”的有力论据。
此外,一些推论有些冒险。在历史研究中,除非引用证据,否则一般不可能猜测古人没有做过的动作。作者引用的韩国和中国学者的作品非常有限,对于整本书主题的更全面、更有力的论证有点遗憾,因为韩国和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已经努力了很长时间,根本不缺创作性的作品。甚至很多中韩同行在具体的理解上也比作者走得更远,比如唐朝及其文明力量,强调百济对日本的深远影响。《天志》一书揭示了更多的字里行间的高级政治的当代考量,即古为今用:日本在7世纪面临着许多国际问题,日本统治者的处理往往毫无意义,因此发动战争、增兵并不明智。这在序言等中也有明确揭示。作者显然有意识地将1300年后白江的失败与二战的失败联系起来。作为一名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我在阅读这样的著作时,经常会反思一个新的问题:在史料相对匮乏、无法建立完整事实链的中世纪,我们是否应该坚持实证取向,在一份史料中说一句话,没有它就不说话?还是单纯把历史当作一种话语,“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把历史评论放在历史考证的包装下?
这些问题可能需要辩论。有争议的观点、方法和范式本身是否正确固然重要,但能否引起争鸣有时更为重要,因为其价值在于提供新的启示,促使人们加深对历史和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