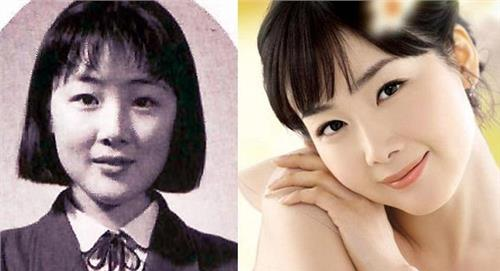班宇 作家班宇:跟故乡任何一条街道都难以产生肌肤之亲

 随着厂区宿舍的拆迁改造,现在很难再有街坊邻居的熟悉感了。除了在秦皇岛读了四年大学,班宇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辽宁沈阳。他大学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沈阳,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去年8月份,现在的班宇全职在家,偶尔写作。小时候,班宇和父母住在变压器厂宿舍,整栋楼里都住了谁,他全都清楚。当时宿舍按照厂区划分,大家在同一个工厂上班,下班后又是邻居,每家每户对于彼此的家庭条件以及脾气秉性都非常熟悉,就像亲戚一样。随着厂区宿舍的拆迁改造,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感受了。长大后的班宇去过很多城市,他发觉这些地方的高铁站、飞机场,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子。现在的城市除了老城区还保有一些特色之外,商圈都很类似。“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被几个包工头改造出来的,城市间有着很强的同质化倾向。在任何一个城市逛夜市,都能吃到大肠包小肠、油炸臭豆腐,好像除了一些自然景点之外,城市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了。”每座城市都建得飞快,在快速城市化后呈现出相似的面貌,生活体验都差不多。“熟悉的东西好像在一点一点离我而去,而当下这些新东西,我既不熟悉也不陌生,它缓缓在我身边生长出来,但就是始终跟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让我跟任何一个地标、任何一条街道都很难产生那种肌肤之亲的感觉。”即便一直生活在沈阳,班宇也会生出一种在故乡里漂泊的感受。
随着厂区宿舍的拆迁改造,现在很难再有街坊邻居的熟悉感了。除了在秦皇岛读了四年大学,班宇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辽宁沈阳。他大学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沈阳,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去年8月份,现在的班宇全职在家,偶尔写作。小时候,班宇和父母住在变压器厂宿舍,整栋楼里都住了谁,他全都清楚。当时宿舍按照厂区划分,大家在同一个工厂上班,下班后又是邻居,每家每户对于彼此的家庭条件以及脾气秉性都非常熟悉,就像亲戚一样。随着厂区宿舍的拆迁改造,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感受了。长大后的班宇去过很多城市,他发觉这些地方的高铁站、飞机场,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子。现在的城市除了老城区还保有一些特色之外,商圈都很类似。“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被几个包工头改造出来的,城市间有着很强的同质化倾向。在任何一个城市逛夜市,都能吃到大肠包小肠、油炸臭豆腐,好像除了一些自然景点之外,城市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了。”每座城市都建得飞快,在快速城市化后呈现出相似的面貌,生活体验都差不多。“熟悉的东西好像在一点一点离我而去,而当下这些新东西,我既不熟悉也不陌生,它缓缓在我身边生长出来,但就是始终跟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让我跟任何一个地标、任何一条街道都很难产生那种肌肤之亲的感觉。”即便一直生活在沈阳,班宇也会生出一种在故乡里漂泊的感受。 每座城市都建得飞快,在快速城市化后呈现出相似的面貌,生活体验都差不多。但如果待的时间够长,就会发现东北人好像要比其他地方的人稍微浪漫一点。除了浪漫之外,可能还能感受到更多的冲突与不同。这就是所谓的缝隙,不会很直观地展示出来,需要在沈阳生活至少三个月到半年,才能感受到。心里有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悬在那里班宇觉得当人们谈到东北的时候,更像谈论一种叙述中的东北,是从公众号或新闻媒体之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特别卡通化的形象——“爱吃烧烤、酸菜与锅包肉,上过九千班,父母经历国企改制,热爱文艺,并且时常眼含热泪。”卡通化就意味着某些特征,鼻子、脸、嘴、眼是高度概括的,是没有深入到毛发和肌肤里面的,是一个最大公约数下还带着点刻板印象的形象。“东北文艺复兴”的论调铺天盖地而来,这或许正是人们对于东北刻板印象的一种集中体现。在班宇看来,东北文艺一直都挺“兴”的,他更倾向于把这句话当成一句玩笑话,可能跟大家都生活在集体环境中有关,过去工厂里经常会组织一些文艺活动,经常有舞会和表演,人们聚一块唱唱跳跳。而且东北人很喜欢表达,无论是通过书写或其他形式,“就好像总要把自己掏出来给大家展示一样,希望自己能在某个时刻闪那么一下光”。在东北文化的基因里,好像总有一个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悬在那里,很多人就会使劲蹦跶,去触碰这个东西,但又轻易触碰不到,就只能不停蹦跶。现在很多东北作品里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他们不会坐在地上打滚,倾吐自己经受了什么苦难,他们能看到一些真正崇高的东西。
每座城市都建得飞快,在快速城市化后呈现出相似的面貌,生活体验都差不多。但如果待的时间够长,就会发现东北人好像要比其他地方的人稍微浪漫一点。除了浪漫之外,可能还能感受到更多的冲突与不同。这就是所谓的缝隙,不会很直观地展示出来,需要在沈阳生活至少三个月到半年,才能感受到。心里有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悬在那里班宇觉得当人们谈到东北的时候,更像谈论一种叙述中的东北,是从公众号或新闻媒体之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特别卡通化的形象——“爱吃烧烤、酸菜与锅包肉,上过九千班,父母经历国企改制,热爱文艺,并且时常眼含热泪。”卡通化就意味着某些特征,鼻子、脸、嘴、眼是高度概括的,是没有深入到毛发和肌肤里面的,是一个最大公约数下还带着点刻板印象的形象。“东北文艺复兴”的论调铺天盖地而来,这或许正是人们对于东北刻板印象的一种集中体现。在班宇看来,东北文艺一直都挺“兴”的,他更倾向于把这句话当成一句玩笑话,可能跟大家都生活在集体环境中有关,过去工厂里经常会组织一些文艺活动,经常有舞会和表演,人们聚一块唱唱跳跳。而且东北人很喜欢表达,无论是通过书写或其他形式,“就好像总要把自己掏出来给大家展示一样,希望自己能在某个时刻闪那么一下光”。在东北文化的基因里,好像总有一个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悬在那里,很多人就会使劲蹦跶,去触碰这个东西,但又轻易触碰不到,就只能不停蹦跶。现在很多东北作品里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他们不会坐在地上打滚,倾吐自己经受了什么苦难,他们能看到一些真正崇高的东西。 在国企改制那段时间,人们聚在一块也尽量不聊工作的事儿。在国企改制那段时间,人们聚在一块也尽量不聊工作的事儿,个体经历太相似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很少谈论近况,因为没必要给彼此添堵。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等轮到自己的时候,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准备了,所以大家看起来并不悲观。班宇很喜欢电影《耳朵大有福》,里面范伟饰演的王抗美是一个刚刚退休、老伴儿生病住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喜欢唱歌跳舞,在工厂里曾是文艺骨干。他从市集上用电脑算命,算出来觉得命不错,还会多给几块钱,美滋滋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他好像真的有一种高于生活的东西存在着,《老人与海》里老头带回来一具鱼骨头仍然是英雄。王抗美生活在各种不顺和局促之间,依然可以在午夜无人的街头高唱《长征组歌》。哪怕在最后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仰面倒在冰冷的大街上,转天他还是能给舞伴打电话,中气十足地喊上一句:“出来跳舞!”班宇与沈阳这座城市之间,似乎还被一条脐带连接着,从来没被斩断过。这条脐带就是东北真实生活中那些琐碎的片段。王抗美是从中活生生走出来的人,在顺流与逆流里辗转腾挪。一位在工人村附近的仙女湖公园跳舞的老人,74岁了,戴着礼帽,每天穿着板正的中山装配大衣,黑、白、灰三套换着穿,即使在沈阳零下近20摄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他已经跳了30多年舞,身体健壮,像个中年男人,每回他戴着墨镜坐公交车,刷完卡听到“滴,夕阳红卡”,周围总会有几个吃惊侧目的,他很得意这点,“跟年轻时候穿白衣服上班一样,有回头率”。老人年轻时,东北作为当时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头顶“共和国长子”的光环,进入国有大型企业的人总是令无数人艳羡。“我在工厂里倒铁水,天天穿一身白,一天一洗,回头率老高了。”
在国企改制那段时间,人们聚在一块也尽量不聊工作的事儿。在国企改制那段时间,人们聚在一块也尽量不聊工作的事儿,个体经历太相似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很少谈论近况,因为没必要给彼此添堵。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等轮到自己的时候,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准备了,所以大家看起来并不悲观。班宇很喜欢电影《耳朵大有福》,里面范伟饰演的王抗美是一个刚刚退休、老伴儿生病住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喜欢唱歌跳舞,在工厂里曾是文艺骨干。他从市集上用电脑算命,算出来觉得命不错,还会多给几块钱,美滋滋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他好像真的有一种高于生活的东西存在着,《老人与海》里老头带回来一具鱼骨头仍然是英雄。王抗美生活在各种不顺和局促之间,依然可以在午夜无人的街头高唱《长征组歌》。哪怕在最后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仰面倒在冰冷的大街上,转天他还是能给舞伴打电话,中气十足地喊上一句:“出来跳舞!”班宇与沈阳这座城市之间,似乎还被一条脐带连接着,从来没被斩断过。这条脐带就是东北真实生活中那些琐碎的片段。王抗美是从中活生生走出来的人,在顺流与逆流里辗转腾挪。一位在工人村附近的仙女湖公园跳舞的老人,74岁了,戴着礼帽,每天穿着板正的中山装配大衣,黑、白、灰三套换着穿,即使在沈阳零下近20摄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他已经跳了30多年舞,身体健壮,像个中年男人,每回他戴着墨镜坐公交车,刷完卡听到“滴,夕阳红卡”,周围总会有几个吃惊侧目的,他很得意这点,“跟年轻时候穿白衣服上班一样,有回头率”。老人年轻时,东北作为当时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头顶“共和国长子”的光环,进入国有大型企业的人总是令无数人艳羡。“我在工厂里倒铁水,天天穿一身白,一天一洗,回头率老高了。” 即使现实变得混乱,他们总能寻找到一丝内心的秩序感与尊严。这是班宇从小最熟悉的生活,他将时代洪流中被改变的命运写进了书里,笔下与现实中的人在两个时空中并行不悖。即使现实变得混乱,他们总能寻找到一丝内心的秩序感与尊严。当年闻名遐迩的工人村,现在只剩下32栋楼,被称作铁西区工人村历史建筑群,曾经的工厂群居式生活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生活仍是跟过去一样热气腾腾进行着。老人们聚在一起唱红歌,一旦有人凑过去,老人们便把歌谱直接展示出来;有人抱着小狗晒太阳,给他拍照就会对着镜头说这是刚捡的狗,花了30块钱在宠物店洗了个澡;大爷大妈围在石台子周围打牌,问一句谁赢了,就把牌往前凑凑,说这把手气不行;菜市场门口卖花生的大妈脸上围着丝巾防晒,常年干活的手虽然粗糙,但还是涂了亮眼的红色指甲油,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旁边卖菠萝的大姨剃着寸头,嘴里叼着烟,据说,越是这样的大姨卖的菠萝越甜。
即使现实变得混乱,他们总能寻找到一丝内心的秩序感与尊严。这是班宇从小最熟悉的生活,他将时代洪流中被改变的命运写进了书里,笔下与现实中的人在两个时空中并行不悖。即使现实变得混乱,他们总能寻找到一丝内心的秩序感与尊严。当年闻名遐迩的工人村,现在只剩下32栋楼,被称作铁西区工人村历史建筑群,曾经的工厂群居式生活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生活仍是跟过去一样热气腾腾进行着。老人们聚在一起唱红歌,一旦有人凑过去,老人们便把歌谱直接展示出来;有人抱着小狗晒太阳,给他拍照就会对着镜头说这是刚捡的狗,花了30块钱在宠物店洗了个澡;大爷大妈围在石台子周围打牌,问一句谁赢了,就把牌往前凑凑,说这把手气不行;菜市场门口卖花生的大妈脸上围着丝巾防晒,常年干活的手虽然粗糙,但还是涂了亮眼的红色指甲油,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旁边卖菠萝的大姨剃着寸头,嘴里叼着烟,据说,越是这样的大姨卖的菠萝越甜。 卖菠萝的大姨剃着寸头,嘴里叼着烟,据说,越是这样的大姨卖的菠萝越甜。城市提供了他熟知的一切班宇跟郑执还有双雪涛这些东北作家,偶尔也会聚在一起吃个饭喝个酒。他们的酒局不会特别指向性地聊文学、聊电影,只是闲聊,然后就开始纯粹地喝酒。班宇讲,他们会喝得很认真,互相监督彼此有没有跟上节奏,有没有少喝、漏喝。谈论到谁的酒量比较好时,班宇说觉得彼此都差不多。他们经常去的那家啤酒屋老伙计上前一提到郑执就竖大拇哥:“老能喝了,10瓶老雪一点问题都没有。”翻看班宇曾经的微博,发现有朋友曾把他称作沈阳鸡架和烧烤专家。当被问到这一点时,班宇说专家谈不上,但确实很喜欢吃,知道很多沈阳好吃的饭店。但是现在很多餐馆从中央食堂进货,味道都变得差不多,他很失望。班宇还很喜欢逛菜市场,他觉得菜市场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很有活力和魅惑性,他非常享受在菜市场里面的感觉。但是现在家里聚会的时候,还是在外面吃的比较多,因为在家做饭一是成本高,食材不便宜;再一个就是收拾起来太麻烦,节假日大家好不容易休息几天,不想太累了。
卖菠萝的大姨剃着寸头,嘴里叼着烟,据说,越是这样的大姨卖的菠萝越甜。城市提供了他熟知的一切班宇跟郑执还有双雪涛这些东北作家,偶尔也会聚在一起吃个饭喝个酒。他们的酒局不会特别指向性地聊文学、聊电影,只是闲聊,然后就开始纯粹地喝酒。班宇讲,他们会喝得很认真,互相监督彼此有没有跟上节奏,有没有少喝、漏喝。谈论到谁的酒量比较好时,班宇说觉得彼此都差不多。他们经常去的那家啤酒屋老伙计上前一提到郑执就竖大拇哥:“老能喝了,10瓶老雪一点问题都没有。”翻看班宇曾经的微博,发现有朋友曾把他称作沈阳鸡架和烧烤专家。当被问到这一点时,班宇说专家谈不上,但确实很喜欢吃,知道很多沈阳好吃的饭店。但是现在很多餐馆从中央食堂进货,味道都变得差不多,他很失望。班宇还很喜欢逛菜市场,他觉得菜市场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很有活力和魅惑性,他非常享受在菜市场里面的感觉。但是现在家里聚会的时候,还是在外面吃的比较多,因为在家做饭一是成本高,食材不便宜;再一个就是收拾起来太麻烦,节假日大家好不容易休息几天,不想太累了。 菜市场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很有活力和魅惑性。班宇目前还是很享受这些的,并没有特别向往过世外桃源,因为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这么一步步城市化建立起来的。他在沈阳长大、工作、结婚、生子,目睹了曾经热火朝天的集体生活,也亲历了熟知的一切逐渐消失,随之商圈和住宅楼盘拔地而起。2002年,铁西区开始“东搬西建”全面改造,那一年,班宇正面临中考。竞争特别激烈,他需要非常努力地学习。在枯燥的学习之外,班宇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放松的方式——逛音像店。那时候沈阳大街小巷遍布大大小小的音像店,在那里能买到正版、盗版磁带,国外打口碟,还可以租售电影VCD。那时候,他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音像店里消磨度过。因为经常去,他跟几个音像店的老板都混得特别熟。他经常跟同学、店员或随便一个逛音像店的人,认真讨论哪张唱片更好听。那是一种浪漫且文艺的体验,可等他上了高中,音像行业基本上就消亡了。网络的兴起,弥补了实体音像店倒闭给班宇带来的遗憾。他喜欢上网逛论坛,逛那种早期的摇滚乐论坛,里面还会有一些读书板块和电影板块。他发现当时很多地下乐队,都会上传自己录的demo小样,供大家听,然后提意见评判。他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发觉不只身边那一小撮人喜欢摇滚乐,而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摇滚乐。当时,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铜镜乐队和隐患乐队。那个时候,虽然大家最开始接触的资源都是欧美的摇滚乐队,但是对于国内的乐队,听到用母语唱摇滚的时候,还是感觉非常亲切。
菜市场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很有活力和魅惑性。班宇目前还是很享受这些的,并没有特别向往过世外桃源,因为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这么一步步城市化建立起来的。他在沈阳长大、工作、结婚、生子,目睹了曾经热火朝天的集体生活,也亲历了熟知的一切逐渐消失,随之商圈和住宅楼盘拔地而起。2002年,铁西区开始“东搬西建”全面改造,那一年,班宇正面临中考。竞争特别激烈,他需要非常努力地学习。在枯燥的学习之外,班宇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放松的方式——逛音像店。那时候沈阳大街小巷遍布大大小小的音像店,在那里能买到正版、盗版磁带,国外打口碟,还可以租售电影VCD。那时候,他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音像店里消磨度过。因为经常去,他跟几个音像店的老板都混得特别熟。他经常跟同学、店员或随便一个逛音像店的人,认真讨论哪张唱片更好听。那是一种浪漫且文艺的体验,可等他上了高中,音像行业基本上就消亡了。网络的兴起,弥补了实体音像店倒闭给班宇带来的遗憾。他喜欢上网逛论坛,逛那种早期的摇滚乐论坛,里面还会有一些读书板块和电影板块。他发现当时很多地下乐队,都会上传自己录的demo小样,供大家听,然后提意见评判。他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发觉不只身边那一小撮人喜欢摇滚乐,而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摇滚乐。当时,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铜镜乐队和隐患乐队。那个时候,虽然大家最开始接触的资源都是欧美的摇滚乐队,但是对于国内的乐队,听到用母语唱摇滚的时候,还是感觉非常亲切。 他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发觉不只身边那一小撮人喜欢摇滚乐,而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摇滚乐。上大学的时候,班宇经常跟同学坐上4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看音乐节,从秦皇岛到北京,只需要22块钱。他记得有一场演出,有两个乐队展示了非常厉害的舞台掌控力,这两支乐队到现在都仍在活跃,分别是“反光镜”和“重塑雕像的权利”。在沈阳铁西区的工业大学附近,班宇也曾花10块钱就能看10支乐队表演,“那时候非常的热血,想看演出、看话剧、看摇滚现场,现在沈阳能看音乐现场的livehouse并不是很多了,自己的兴趣也慢慢减弱了”。写作已经成了一个规定动作“年少时信奉许多没有来由的力量,并为之战栗、激动,想象着抵抗与超越,不在乎误解。”提到这种没来由的力量,班宇觉得就很像摇滚乐里面的冲动,伤感和怨愤积攒在一起,特别想要冲撞出去。而对于外界嘈杂的声音,班宇曾经也困惑过,但现在不会了。因为他知道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既然已经来到只顾着匆忙自我表达的时代,那就不要去管那么多声音了,要多静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声音。在刚写完《冬泳》后,班宇偶尔还会翻看豆瓣评论,到了第二本就很少看了。别人的评价和观点也很难影响到他,他只想用一种漂亮的方式写一些舒服的句子出来。写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在脑海中立一个相对模糊的形象,可能是一个朋友、演员或者代入自己。之前易烊千玺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冬泳》的书封,导致该书多次加印,班宇也曾在微博上感谢过易烊千玺。问及未来《冬泳》影视化会不会想要和易烊千玺合作时,班宇表示小说创作跟影视化是两件事情,在那个领域他不是专业人士,也不太想去做编剧,觉得那是另一个工种,自己可能并不擅长。
他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发觉不只身边那一小撮人喜欢摇滚乐,而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摇滚乐。上大学的时候,班宇经常跟同学坐上4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看音乐节,从秦皇岛到北京,只需要22块钱。他记得有一场演出,有两个乐队展示了非常厉害的舞台掌控力,这两支乐队到现在都仍在活跃,分别是“反光镜”和“重塑雕像的权利”。在沈阳铁西区的工业大学附近,班宇也曾花10块钱就能看10支乐队表演,“那时候非常的热血,想看演出、看话剧、看摇滚现场,现在沈阳能看音乐现场的livehouse并不是很多了,自己的兴趣也慢慢减弱了”。写作已经成了一个规定动作“年少时信奉许多没有来由的力量,并为之战栗、激动,想象着抵抗与超越,不在乎误解。”提到这种没来由的力量,班宇觉得就很像摇滚乐里面的冲动,伤感和怨愤积攒在一起,特别想要冲撞出去。而对于外界嘈杂的声音,班宇曾经也困惑过,但现在不会了。因为他知道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既然已经来到只顾着匆忙自我表达的时代,那就不要去管那么多声音了,要多静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声音。在刚写完《冬泳》后,班宇偶尔还会翻看豆瓣评论,到了第二本就很少看了。别人的评价和观点也很难影响到他,他只想用一种漂亮的方式写一些舒服的句子出来。写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在脑海中立一个相对模糊的形象,可能是一个朋友、演员或者代入自己。之前易烊千玺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冬泳》的书封,导致该书多次加印,班宇也曾在微博上感谢过易烊千玺。问及未来《冬泳》影视化会不会想要和易烊千玺合作时,班宇表示小说创作跟影视化是两件事情,在那个领域他不是专业人士,也不太想去做编剧,觉得那是另一个工种,自己可能并不擅长。 班宇小说《冬泳》。班宇写小说并非心血来潮,在尝试写小说之前,他很早就开始了写作,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写作已经成了一个规定动作,他并不担心有一天会丧失表达欲,觉得如果没有了也不一定是件坏事。班宇曾经参加过一个盛典,并在第二天写了篇文章,形容名利场就像一场台风。现在盛行的“流量”似乎也是如此。谈及流量,他觉得流量是假的,数据也是假的,只有人才是真的。“人才是一个最大的流量场,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像从你身上飞驰而去的1和0,只是单纯的数字,这些会匆匆地飞驰而去。而人要把自己变成那些1和0,这才是最重要的。”近来,班宇正在创作新小说,谈及叙事主体,他说从来没有刻意地要围绕东北创作。只不过之前信手拈来的背景或者人物对话方式,是更让他熟悉的方式而已,在第二本《逍遥游》里,就已经不怎么围绕东北展开了。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班宇回忆过去发生的一切,经常会感到不真实。但在这种剧烈的变化中,回忆可能也是他唯一能把握住的东西了。他很珍视,也很怀念。这让人不由得想到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描述的:“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
班宇小说《冬泳》。班宇写小说并非心血来潮,在尝试写小说之前,他很早就开始了写作,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写作已经成了一个规定动作,他并不担心有一天会丧失表达欲,觉得如果没有了也不一定是件坏事。班宇曾经参加过一个盛典,并在第二天写了篇文章,形容名利场就像一场台风。现在盛行的“流量”似乎也是如此。谈及流量,他觉得流量是假的,数据也是假的,只有人才是真的。“人才是一个最大的流量场,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像从你身上飞驰而去的1和0,只是单纯的数字,这些会匆匆地飞驰而去。而人要把自己变成那些1和0,这才是最重要的。”近来,班宇正在创作新小说,谈及叙事主体,他说从来没有刻意地要围绕东北创作。只不过之前信手拈来的背景或者人物对话方式,是更让他熟悉的方式而已,在第二本《逍遥游》里,就已经不怎么围绕东北展开了。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班宇回忆过去发生的一切,经常会感到不真实。但在这种剧烈的变化中,回忆可能也是他唯一能把握住的东西了。他很珍视,也很怀念。这让人不由得想到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描述的:“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
沈阳街景。站在城市版图上的班宇,回忆并瞭望着与这座城市有关的过往与未来,同时,低下头,他又不得不与各种琐碎搏斗。比如,要克服惰性,他自认不算特别勤奋,每天能写三四个小时都算很多了;工作和创作时必须去工作室,“在家里太容易懒惰,离床太近了”。再比如,从2016年年底开始,班宇背上了终其一生的甜蜜负担,成为父亲。养育女儿的日常点滴也让他开始不可免俗地思考教育的问题。谈及这代孩子和自己的不同,班宇说自己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是爷爷奶奶带大的,而现在的小孩很早就开始上幼儿园了。他的小说《肃杀》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失业之后的爸爸买了辆二手摩托车,日子过得不富裕,但还是会挤出钱来送孩子去上提高班。即便不靠谱的人对培养孩子特长也很上心,“肖树斌正坐在我家的阳台上喝酒,他侧着身子,手里举着筷子,满脸通红,唾星飞溅,朝我爸比划着说,这么大一个金镏子,给送过去了,就他妈让踢十五分钟,黑不黑。我爸说,没办法,培养特长就是费钱”。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那个年代的父母都极尽所能地把孩子照顾好,哪怕遇到难处,手里没钱,亲戚间互相帮衬,也总能找到办法解决。对于女儿的教育,班宇不会要求孩子学很多的东西,开心最重要。女儿现在非常喜欢看书,很喜欢读绘本,会说一些很有意思的句子。前几天他在家里看书,女儿喊他,他没有听见,女儿就跑过来说:“爸爸,我的呼喊穿过了整个宇宙。”有一次班宇把女儿手里的东西拿过来,女儿说:“现在我两手空空,只好攥紧自己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