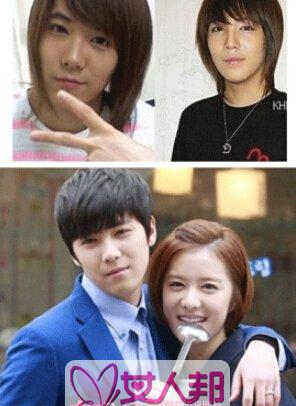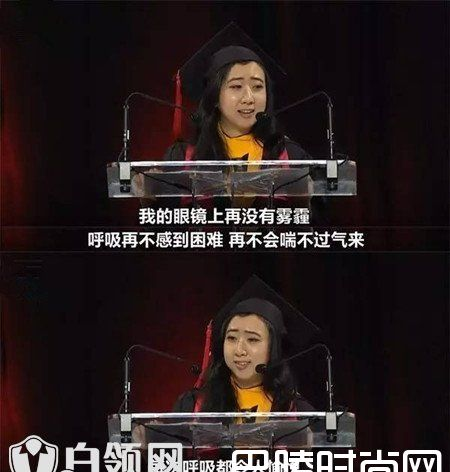复旦大学历史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42岁女教授司佳逝世 曾师从周振鹤
据多方消息,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司嘉于2020年10月11日晚因病去世,享年42岁。
司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兴趣还包括上海近代城市社会,出版史、文化史及阅读史。多次给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学位专业、选修课程,以及全英语课程教学,尤其注重在授课内容中强调中英文原始资料的解读与运用。着有《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出版译作《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并发表论文三十篇。1995年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考入复旦大学第一文科基地班。1999年至2001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得威廉·佩恩奖学金全额奖学金,赴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8月获得该校博士学位。2001-2002年,他被评为美国汉尼基金会的年轻学者。从2006-07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担任讲师,并在圣约瑟夫大学历史系担任助理教授。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16年11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2010年赴日本岱西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G-COE项目博士后研究。2008年获上海陈光学者基金;2014年获“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教学示范课”。
司佳论着目录学术专著司佳,《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10月。司嘉,《英语在中国的传播:演讲者、历史文本和新的语言景观》。VDM出版集团,2009。编着、译着阿诺德·汤因比,《中国之旅: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司 佳、徐亦猛 编《近代东亚国际视阈下的基督教教育与文化认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学术论文:1.司佳,《伦敦会藏梁发〈日记言行〉手稿解读》,《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3期,第130-135页。2.司嘉:《从日记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22-130页。3. SI Jia Jane, and Dong Shaoxin, “Humanistic Approach of the Early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51.1 :100-112.4.司嘉、晁德利:《清代圣言的拉丁翻译》,《复旦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5. 司佳,《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中文作品与翻译策略:以米怜为中心的讨论》,香港《翻译史研究》2015年12月出版。6.司嘉,“现代基督教的三字经与中西语言文化的接触”,《或问》,第38期,日本现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协会,2015年12月。7. 司佳,《文本、书院与教育:伦敦会在早期在马六甲的对华传教准备工作》,《澳门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81-90页。2015年第1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全文转载,78-86页。8.19世纪上海的通商口岸英语:演讲者、声音和图像交叉潮流:东亚历史和文化评论,6 : 38-66。9. 司佳,《邝其照与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兼谈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及其历史实用价值》,《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149-158页。10.司嘉:《传教士为何研究:美国卫三畏家族档案手稿札记》,士林,2013年第3期,第90-97页。11. 司佳, “Reprinting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arket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科前沿》,6.2 :229-242.12.司嘉:《基督教女性三字经初探:以训女三字经为例》,《东亚文化谈判研究》2011年第4期,第243-252页。13. 司佳,《耶鲁大学传教士档案所见清代圣谕广训方言手抄稿若干种》,日本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或问》第21号,2011年,117-128页。14.司嘉:《马多克斯的三字经与中国及南洋早期新教活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第112-119页。15. 司佳,《见闻、谈资与讽刺诗——中国洋泾浜英语在十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传》,《九州学林》2010年,172-189页。16.司嘉,“收集与收藏:罗伯特·莫里森词典中的中国本土文化”,复旦学报,4: 104-122。17. 司佳, “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4.3 : 340-357.18.司嘉:《吴赋再版与19世纪中后期的上海英语出版业》,,第2期,2009年,第6-13页。19. 司佳, “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 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 1 : 126-143.20.贾珍思:“辞书谱系:生产者、文学受众与上海通商口岸的英文文本流通。”中国-柏拉图论文,151。21. 司佳,《邝氏英学丛书与十九世纪末上海实用英学形成》,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2005年,第80-90页。22.司嘉:《商人、仆人、总务与18世纪中国沿海地区洋泾浜英语的形成》,或《瓦库蒙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研究杂志》,第6期,85-93页,日本代西大学。23. 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换》,《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44-50页。24.司嘉,“西方人在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中的作用”,香港《语言建设通讯》64: 11-19。25. 司佳,《从岁时到天时:明清移民以后土着苗民之日常生活安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35-48页。26.司嘉:《早期英汉词典中的语言接触现象》,《复旦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60-67页。27. 书评 Book Review.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 al.中国学术, 2 : 271-73.28.书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及其向民族语言的演变。费德里科·马西尼。中国学术,2: 340-43。重发司老师旧文,深表哀悼。解读梁发《伦敦日记·言行手稿》司佳摘要本文试对英国伦敦会案卷中所藏之梁发1830年《日记言行》手稿进行校订、整理与解读,并结合历史语境进行文本分析,探讨其作为稀见史料在十九世纪早期汉语基督教文献结构中的位置与意义。作为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助手或"中间人物",梁发撰写的这本历时八个月的日记事实上乃是一部工作"日志"。在日志中,梁发围绕1830年"科举分书"活动的前后进行展开,不仅对宗教小册的撰写、印刷、分发情况有详细记载,且亦多处提及其自身的宗教活动,包括对宗教书籍的阅读、讲授,并涉及基督教与中国南方本土信仰的对话与辩论。这份日记材料所反映出的宗教观念思想还可以为研究梁发《劝世良言》作品的形成提供互证。关键词:梁发;伦敦会议;日记言行;中国基督教文学;科举分为书;传教士一、引言近年来,随着海外文献和手稿的发掘,19世纪初新教传入中国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其中,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受众的关系、早期皈依者的生活经历及其与海外华人宗教团体建立的背景等研究课题备受关注。研究路径从单向度的宗教史层面拓展到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文学翻译、宗教与文化传承等多向度的课题。,而研究对象的价值认同也变得多元和多样。例如,作者近年来的作品更多地接触到早期新教历史中相同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多语言档案。其中,梁发作为中国早期新教皈依者之一,由于史料的语言和性质不同,其形象和评价也不尽相同。第一位为立传的传教士麦占恩认为,梁独特的经历和精神资源为华南地区的新教活动铺平了道路。如果仅以的《世界的劝导》一书作为评价其思想历程的核心,他们大多会注意到梁作品中的宗教表达多来自于他的外教,并没有太多独到的见解。最多是结合一些“本土化”问题用中文表达。然而,如果我们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中间人物”来理解梁发的经历和作品,或许可以为中国早期基督教文学的审视增添一笔特别的笔触。因而,如何理解这些在宗教关照下获得特殊经历的 “中间人物”? 或许一手档案史料能够帮助研究者更贴近研究对象的内心,加以“同情之理解”。笔者曾于2017 年第 6 期《近代史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在研究过程中,亦对现藏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的一部梁发日记手稿做了比较详细的校订工作。然而限于发表篇幅,该文未能对这部历时近八个月、篇幅逾三万字的日记具体内容作过多展开。承蒙贵刊邀约,兹将这部日记手稿以附录形式作为研究资料分享,并重点对梁发《日记言行》上半部分作如下解读与勘校。▲梁发的日记言行
二、 小书日记言行主要记述了1830年3月5日至同年9月21日梁发的日常宗教活动。包括在广东给当地人讲授圣经章节,尝试初步讲道,出版几本自己写的宗教小册子,跟随省学政,沿科举路线开展“拆书”活动。那一年,梁发41岁,这是他一生在中国开展活动的重要阶段。这本日记很可能是梁发自己或别人抄的,字迹工整清晰,只有几处改动,总长度超过30页。梁发在日记中也有几处提到,他有时“在店里看书写日记”或“在林厅写日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写这篇日记是作者的一次特殊的记录活动。在同一个文件夹中,附上了马礼逊写的英文介绍,并翻译了一些段落。主要目的是向伦敦会议总部展示这位19世纪早期中国新教徒的“足迹”和“成就”。早年当过印刷工的梁发,去南洋辅佐传教士米利安,在马六甲的华英学院学习宗教课程。1822年米利安去世后,梁发离开马六甲,在澳门和广东停留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梁发致力于神学知识,不时从马礼逊发函交流和报告自己的阅读经历,并开始撰写《寻求真理之源》、《解释真理》和《他律》等宗教小册子。梁日记的前半部分提到了这些小册子的写作,这几章的内容与的其他作品一起构成了《劝导世界》。因此,日记所记 1830 年前后,梁发正由一名笃信福音的 “学生” 逐步转变为能够独立阐述基督教经典的 “作者”。尤其在梁被马礼逊封立为“传道人”后,他不仅劝说自己的妻子以及多名族人皈依了基督教,还承担了着书、刻书、印书、分书等要务。这里的“书”指的是宗教小册,梁发时而称之为“小书”,是十九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文字布道”的重要介质。梁在马六甲英华书院时,其宗教课程内容除了研习《圣经》篇目,另一主要方式便是学习当时传教士编写完成的小册,如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幼学浅解问答》 等,以之为读解 《圣经》的辅助材料。在《日记言行》中我们看到,这些十九世纪早期“文字布道”的奠基作品经梁发之手,于其家乡广东高明县周围逐渐传播开来,尽管这在清廷禁教的大背景下是极其艰难的,随时可能遭受牢狱之灾。梁亦多处提及他与助手屈昂“印书接书”、“钉书裁切书”,其中即有米怜在马六甲所着之《两友相论》和《灵魂篇》这两种小册。当然,还有几种乃梁发自己的作品。梁发19世纪30年代的分书经历以及《劝世》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联系,过去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专门的论文中有所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日记·言行录》记录了1830年农历四月至六月梁发的分书经历,详细记录了科学研究分书的具体路线和每届分发的小册子数量,显示了日记手稿的特殊历史价值。作为早期重要的华人新教徒,梁发对撰写基督教中文作品的坚定热忱众所周知,而他的日记中也多次提到这段关键的1830年前后的着书经历。然而,从 “阅读史”角度来看,《日记言行》亦记载了梁发在这八个月期间,除平日讲道、着书、分书等活动外,他反复研读的是哪些书作——这在来华传教士档案史料中更是难得一见。在日记中,常有 “在家看书写字”的记录,并时而出现具体的书作名称。梁发阅读的主要是《圣经》中的篇目,或作为巩固自身信仰的方式,或作为向听众讲道前的文本准备。通观日记全文,梁发不仅提及了《新约》中的所有篇目,即《马窦书》、《马耳可书》、《路加书》、《若翰福音书》、《使徒行书》、《罗马书》、《可林多》、《厄拉氐亚》以及 “《以弗所书》至《现示》各书”;他还认真研读了《旧约》的大部分篇章,如《创世历代书》、《利未氐古书》、《算民数书》、《若书亚》、《以世得耳传》、《若百》、《谚语》、《所罗门书传》、《十二先知传》等等。三、作者作为对基督教中文作品做出一定贡献的中国新教徒,梁发的生平概况及其大部分的着作简介 被收入于伟烈亚力的《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纪念回忆及着作目录》中。或许缘于梁发是“传道人”,非伟烈亚力书名中所列之“传教士”, 因此他的着作词条并没有一个单列的位置,仅附于米怜的生平贡献之后。而梁发着作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或可代表十九世纪最早皈依的中国新教徒对基督教经典的一种阐释。同时,比对这部日记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由于文本多处反映出作品被释读的一种“实践”过程,梁发的 “着书” 与 “分书”、“解书” 等一系列活动实乃互动关联的。梁在向广东本地百姓分书讲道的过程中,及时融入了他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思考的问题,并将多半晦涩难懂的宗教书面文字化解成为“本土化”的概念与道理。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日记言行》中所呈现出的对话内容,有些乃基于梁发《求福免祸要论》、《真道浅解问答》等作品,有些则直接出自其师米怜的着作段落。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及时调整话语,尽量使自己口中的“道理”既有基督教文本依据,又适时加入中国南方民间信仰的语汇。比如《日记的言行》开门见山,直指19世纪初新教与中国本土信仰文化“对话”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一神”、“灵魂”和“永生”。梁发多采取集中不同文章,隔几天对特定宗教概念进行教学和阅读的方式;同时,在他的作品中,这些信念的关键词在“文本实践”的过程中是相互关联的。《日记》中提到的第一件事,是1830年农历三月,梁发和“陈某”在广东省会出租屋里的几次对话。这位姓陈的男子从事刻字生意。听了几次梁发对十诫的解释,他觉得自己离基督教的教义标准还很远。他直言,如果你遵循“你说的,我的刻字业务大部分都不应该做”的原则。陈某对信仰的关注主要是出于保护世界财富的心理需要。换句话说,“你讲上帝和上帝的真理,太好了。等你信了以后,你就一天比一天有钱了,家里每个人都没有灾病了。”梁发在这里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而是将基督教“福音”的“福”与世俗的“福”区分开来,用“救赎”的概念来帮助解释信仰是为了在下辈子得到“永远的福报”。梁发这样回应:“你想发财,而不是一个相信上帝真理的人。信上帝、天、神真理的人,知道自己有罪,请求宽恕,内心宝贵的灵魂是永生,永远的不幸有报应。”如此,梁发即引出了 “灵魂”这两个字,并与基督教 “十诫”中他所表达的 “休息日不可 做工”这一条联系在一起,告知陈某不应当做工是由于 “需保养灵魂”。当然各种宗教关于“灵 魂”的概念与阐释都是大而复杂的问题,在《日记言行》中亦不止一次提及如何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待“灵魂”的特殊性 ——即与“身后世界”、“来世报应”紧密联系的一种理解,并将之区分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中的 “灵” 或 “魂”。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五月梁发与屈昂到达广东高州时,梁曾遇到一位旅舍店主,专门向其询问“灵魂系样何物”。梁发的回答依据的主要是米怜所着《张远两友相论》里的说法。笔者在此前发表的文章中已有举例,这里不再赘述。当像陈某这样关注眼前利益的人不坚定地追求信仰时,梁发的说服方法或技巧之一就是将问题的认知角度转向反面。在《日记·言行录》中,梁多次反对“福”与“祸”作为信仰的结果,并强化了二者之间可能的转化关系,即“福祸”与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报应论”有关。这种说法与他当时正在写的一部作品《论求福避祸》直接相关。在写作的过程中,梁发还融入了自己的一些写作想象,如“求福避祸”、“呼唤灾难”等。,这可能在原始圣经中找不到。梁笔下的“福”字,指的是福。作为固定名词,有时写成《圣经》中的福报,作为形容词,则是混合或混成,即基督教的福音。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梁发觉得很难向普通人解释基督教福音的祝福——因为在中国本土的信仰中,几乎没有一套宗教理念可以对应对来世的关怀,比如“原罪”、“救赎”、“灵魂”和“永生”。在当时梁发生活的社会环境中,他周围的人大多是靠做小生意为生的普通人。他们大多数人在被打击时,把“福”理解为世俗的财富或“福”或“福”。他们一般也会去寺庙烧香拜神拜佛,祈求保佑这个世界吉祥如意。因此,从《日记·言行录》前半部分梁发与普通人的多次对话记录来看,“求福避祸”可以看作是一个结合本土信仰的试探性词汇。四、听众《日记言行》中出现的听道者有黎、李、王、何、张、颜、杨等七人。而据梁发自己的记载,跟他交谈过一次以上的有陈某、陈老三、李新、林某及其兄弟大亨概五人。在沿途 “分书”过程 中,梁还与“单”姓与“允”姓的两名店主以及渡船上遇到的“关某”略作交谈。另有一位“老先生”,虽然日记中没有记录下具体谈话的内容,然而从《日记言行》一开始的部分来看,梁发专门去了“老先生”的住处同其商谈“分书”计划并从他那里得到六十圆的资金支持。梁分书结束后回到省城又与其有过一两次交往,比如全文最后一句所说“早拜神毕,食饭后往老先生行内”。麦沾恩在《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一文中称,伦敦会案卷中的这本梁发日记,始记于 1830年3月28日“即在马礼逊先生家中与美国人会晤之后数日起”。由此便可对照,这位“老先生”应当就是马礼逊。上文提到,1822 年米怜去世,不久梁发离开马六甲,此后赴澳门、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并投入大量精力研习中文宗教小册的写作。1827至1829年,马礼逊曾多次致书伦敦会报告关于梁发的工作,大力赞赏梁为撰写、印刷布道小书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日记·言行录》有李、李、王、何、张、阎、杨等七位听众。根据自己的记录,、陈老三、李新、林以及他的兄弟大亨都不止一次与他交谈过。在一路上“分书”的过程中,梁还与在渡口相遇的“丹”“云”“关”两位店主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还有一个“老先生”。虽然日记中没有具体的谈话记录,但从《日记·言行录》开始,梁发就去“老先生”的住处与他商量“分书”的方案,并从他那里得到了60元的经济资助。梁奋书回到省城后,和他有过一两次接触。比如全文最后一句所说的“尽早拜上帝,吃完再去找老君”。在《中国最早的传教士梁发》一文中,麦占恩说,伦敦会议案卷中的这本梁发日记开始于1830年3月28日,“也就是在马礼逊先生家中与美国人会面后的几天”。相比之下,这个“老人”应该是马礼逊。如上所述,米利安死于1822年,不久之后梁发离开了马六甲。之后,他赴澳门、广州与马礼逊留学,并投入大量精力研究中国宗教小册子的写作。从1827年到1829年,多次向伦敦学会报告的工作,并对梁在撰写和印刷布道文方面的辛勤工作表示赞赏。
▲马礼逊和梁发
《日记言行》 中连续近八个月的纪实性文字,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所涉人物之性格。在信仰面前,梁发表现出一名虔诚基督徒的处事方式,关键之处尤能彰显其正直果断的一面。从初次与听道者的交谈对话中也可以看出,梁发并没有因一味需求 “功绩”而随意改变 “信”的必要条件。当他发现与对方毫无继续沟通之余地时,便断然离开,评说亦直接了当,如“陈某满腹贪财之心,好色之人,不是奉信真道之友”。但是,当遇到有意愿进一步听其讲述经文的慕道者,梁发会耐心地与之多次交谈。例如四月二十一日梁发与屈昂在“分书”活动途经高州府时,于一歇店住宿二十日余,与一名叫 “陈老三”的店主有若干次关于敬拜方式及 “灵魂” 的讨论。又, 五月二十四日他们到达省城入住“林馆” 后,即刻将小册分发到住客手 中,几日后馆主“林某” 便产生了兴趣,多次向梁发讨教“耶稣受难”、“救赎”等他不解的“真经之义”。数次交流之后,林某向梁发袒露了此前欲入佛教当僧人的想法,梁又立即与他分享了自己亦曾信佛但最终被基督教“感化了心” 的心理过程,并将此处“佛耶”竞争中佛教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佛家没有对“罪”与 “过”的反思,仅注重念经及烧香送银。梁此处驳斥佛教的语气尤其坚定,如“且问参禅打坐,有益于佛,还是有益于人?”并进一步说 “佛家的诡计,样样经典,都系哄骗人钱银”。从而引导林某“知佛教之害,信真经之益”。在林中会馆住了20多天,完成了“科举制分册”的任务后,梁发于6月底回到高明县作短暂停留。不久,他对妻子说:“因为上个月在全省分发圣书的时候,有一个叫林的人很喜欢我,听了《神与天福音》的真理。我回到林家,尽力说服他真相的各种含义。...他信不信,尽我的职责。“我想让从林之前的表现中推断出他还有空的信仰转换。这一次,两人根据《使徒行传》、《伊斯卡利加》和《德米特里厄斯》等圣经文章,深入讨论了“真正的活神”、“圣父、圣子、圣风”和“宝贵的灵魂”等关键概念。在反复宣讲的过程中,梁发果断地在关键点上阐述了“先信后明”的重要性:“凡信真经者,先信后明。现在你首先要理解和相信。恐怕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以后你会越来越多疑,对信仰不尊重。”然而,日记中用墨较多的“牟林”和“李信”的例子似乎给读者留下了伏笔。在《日记·言行录》中,我们不知道林、李是否因为的影响而成为中国早期的新教徒。林在受洗问题上犹豫不决,说要“明白圣书的意思才敢接受洗礼”,然后以回家看母亲为由推脱。后来,九月初四,第三次到省城,再次问起,林说他之所以一直不敢接受洗礼:“因为我父亲现在做生意,卖元宝纸。如果我受洗并相信耶稣,我就不能做这件事。之前一直在林厅听讲座的水泥工人李欣主动询问洗礼的意义和规则,但听了梁的解释后,他怀疑“这就是洗礼的规则?”此外,他还说:“我估计你还有其他奇怪的规矩”,“要慢慢想,我才会受洗礼入道”。据麦占恩先生说,几个月后再路过广州时,立即同时给林和李信施了洗礼。这一方面证明了1830年梁发在“科举制”和个人传教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梁的说教方式是建立在尊重听者个人意愿的基础上的,他以严肃信仰的原则对待听者,尽管他参考了当地的语境或在某些地方使用了类比和隐喻。比如梁发对李信说,受洗之后,“上帝把你算作他的义子。如果你身上有印记,你会一直照顾你,你不会被恶灵诱惑去做坏事,而是暗中帮助你做好人。”《日记·言行录》为我们提供了梁与道教仰慕者多次对话的全部文本细节,不仅深入浅出,而且在信仰冲突、思想曲折等诸多地方充满了一种“张力”,真实地展现了皈依者的心路历程。五、结语在向当地普通民众传授基督教信仰时,梁发偶尔会提到他“用上帝和上天赐予的所有才能来宣讲”——这可能是一种描绘信徒虔诚之心的说辞。但事实上,这本历时八个月的日记,记录了梁多次“失败”的尝试。表面上看,梁发除了“分册”之外一切顺利,其他几次布道都没有结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反映了早期新教“词讲道”在中国的艰难处境。因此,在利用之前所获得的宗教知识进行传教和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调整”的策略和“想象”的话语,这是个人思想和文本知识结构在实践过程中的一种调整——这体现在他的日记中多处记载的梁与当地人关于信仰习俗的对话和争论中。梁发、瞿昂等早期中国新教徒无疑面临着强大的宗教竞争对手,而他们自身的能力则受到复杂形势的挑战。结合梁在1830年前后所写的各种宗教小册子,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劝导良言》,我们还可以从《日记·言行录》中追溯所写的“一神、福、祸、罪、赎、魂”等基督教关键观念的来源。因此,从文本功能来看,《日记·言行录》不仅仅是记录言行的日记或日志。通过相互认证的方法,这份日记材料还可以与传教报道联系起来,区分和比较早期中国基督徒在新教传教士眼中的“形象”和“行动”。作为学术工作者,在处理第一手档案和手稿时,也需要区分它们写作的目的和作用,从史料、历史、宗教等角度分析中外宗教信仰的竞争。本文对梁发在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撰写的1830年3月28日至9月18日的原始手稿进行了整理和出版,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原标题:《逝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42岁女教授司佳逝世,曾师从周振鹤》